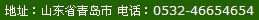|
白癜丸价格在哪个价位区间 http://www.ksfences.com/朝开铁路,夕死可矣李鸿章谋划修建铁路的一个插曲中国有可富可强之资,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亦必富强而后可以居中驭外,建久远不拔之基。——李鸿章一掐指往前推算,一百二十多年前,中国的陆地交通工具中,没有动力车辆,旅行只能依靠畜力或者脚力。外国人记录说:“在天津、北京之间的八十英里路程上,大批旅客要付六元至九元雇一辆车子,走上两天。”而在实际上,人们花费的时间还要更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当时马车旅行的方式:一般来说,商人都乘坐一种有盖的小马车,一天行驶大约三十英里。他们在拂晓前大约一小时开始一天的行程,一直走到十点左右,然后停下来喂骡子,吃中午饭;十二点左右,他们再次上路,走到薄暮才停下来。这种交通方式,与两千年前孔子周游列国,几乎没有区别。当然也可选择坐船。年9月28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慈禧太后命翁同龢秘往天津,与李鸿章商量和战大局。翁同龢带着三个男仆和一个打杂的下人微服出行,早晨过崇文门到东便门,再到二闸,雇舟经平上闸、平下闸、普济闸,中午抵通州上岸。下午至盐滩觅一小舟,顺流一百里,黄昏到达马头。次日寅初船行,天明过香河,辰初过红庙,辰正过河西务,午过蔡村,未正抵杨村,抵暮过王新店,戊初泊北仓。第三日卯初,船再开驶,日出过丁沽,辰初抵达天津吴楚公所,全部行程二天有半。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自年代,蒸汽火车在英国被发明并投入商业使用。现代火车之父乔治·史蒂芬森(GeorgeStephenson)出生于年,自幼家贫,没钱念书。他17岁去煤矿做工,自己花钱在夜校学习了读写,此后辗转多个矿井并逐渐成为蒸汽机械方面的专家。年,史蒂芬森设计了他的第一台蒸汽机车用来运输煤炭。在之后的数十年间,他提出标准轨距的概念,还为多条铁路设计了蒸汽机车并不断改进技术。年10月,利物浦至曼彻斯特的铁路接近完工,铁路公司的董事们组织了一场比赛,以决定谁的蒸汽机车将用来连接当时英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共有五名参赛者参加了这场蒸汽机车早期发展史上的重要比赛,史蒂芬森亲自驾驶他的“火箭号”(Stephenson’sRocket)以30英里的时速成为唯一完成全程的胜利者。此后,火车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交往,铁路作为那个年代最有诱惑的投资标的,在欧洲和美洲大陆被快速地推广开来。年2月12日,总理衙门致函各地封疆大吏,谈及海外各国公使,都在推动中国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线,而被中方婉辞。“中国地势与外洋不同,倘任其安设飞线,是地隔数千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如开设铁路,洋人可任便往来,较之尽东其亩,于大局更有关系。”总理衙门要求,嗣后各国领事如有向地方官请求立电线开铁路等事,须“力为设法阻止,以弥衅端而杜后患”。并要各地大员表明态度。在总理衙门大臣看来,铁路、电报若在中国使用,得益的是外国人,于中国不仅无关,还要受其伤害。一个月后,江苏巡抚李鸿章回信,表示“铁路费繁事巨,变易山川,彼族亦知断不能允,中国亦易正言拒绝”。江西巡抚沈葆桢也说:“平天险之山川,固为将来巨患;而伤民间之庐墓,即启目下争端。”李、沈都是当时巡抚中的后起之秀,但他们对待铁路,均持保守态度。两广总督毛鸿宾亦回信表示:开铁路则必用火轮车,方可驰骋如飞。无论凿山塞水,占人田业,毁人庐墓,沿途骚扰,苦累无穷。而此路一开,遂专为外国火车独行之路,中国车马既难与之并驾齐驱,更不堪其横冲直撞,势将断绝往来,商民交困。诚如指示,于中国地方大局种种关碍,实属断难准行。且内地股匪未靖,伏莽滋多,遇此等惊世骇俗之举,乘机煽动,作梗生端,即外国人之在中国者,亦断不能平安无事。而设此铜线、铁路,需用数百万巨项,岂不徒事虚糜,是于外国人亦有损无益。去年接晤英法各国驻广领事,曾经闲谈及之,当即将中国地势民情与外国大不相同之处,并中外均有不便各缘由,详细开导,切实指陈;该领事等似颇领会,俱各俯首无词。本年迭次会晤,无复以前事为言。……但不可不预为之防。现已遵照钧示,密饬所属,随时体察,实力阻止。这些中国官员,生平尚未见到过火车,却很有把握地断然认定铁路不合中国国情。山川墓庐等等,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祖先的和谐相处,如此高妙的话题,成为反复用来论证或搪塞的理由。毛鸿宾声称,经他“详细开导,切实指陈;该领事等似颇领会,俱各俯首无词”,则是天朝官员惯有的自说自话的一面之词。年底,总理衙门收到英籍总税务司赫德呈递的建言《局外旁观论》:“矮人立于长人肩上,所见必远于长人。庐山真面,惟在山外者得见其全”。中国通赫德劈头就用了李白诗句的典故,他写道:“凡有外国可教之善法,应学应办。即如铸银钱以便民用,做轮车以利人行,造船以便涉险,电机以速通信。外国之好法不止四条。然旁观劝行之意不在此,系在外国日后必请之事。”赫德所陈请者,为现代化国家之重要基础,即金融、铁路、造船、电信,但依然未获清政府的
侍生 张佩纶顿首二月朔日 上海舟中荣曾见杨守,如无暇,先令杨守见之亦可。显然,在推荐幕友荣俊业的时候,张佩纶是认真、周到、细致的。荣俊业,字履吉,号琴斋,无锡西郊荣巷人。经张佩纶推荐,他成为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文案,后因帮助候补道朱仲甫获得广东厘金局三水口总办实缺,朱遂任荣俊业族侄荣熙泰为其总帐,成为世交,荣氏亦由此逐渐发家。荣熙泰的儿子叫荣德生,荣德生的儿子叫荣毅仁,荣毅仁的儿子叫荣智健。这个后来显赫无比的家族在回溯历史的时候,每每不忘荣俊业对荣熙泰的提携,但却似未注意到,荣俊业之所以入幕张之洞,其实来自张佩纶的举荐。信中所提“恪靖转遭严饬”,是指左宗棠奉旨调查中法马尾之战情形,为张佩纶做了辩护,指出“马江败后,居民一日数惊,众论纷歧,道听途说,既可任意以增加巷议街谈,岂顾情事之虚实?京员据闽信以入告,而不知闽信多本于乡人激愤之词也。伏维圣明在上,前此迭降谕旨,赏功罚罪,权衡轻重,大体攸关。其他传闻失实之事,自可置之勿论”,转而招致朝廷传旨申饬之事。以左宗棠地位之尊,也无法帮助张佩纶逃脱被弹劾流放、从此退出政治舞台的厄运。张佩纶在赴戍途中为师爷写的推荐函,不经意间,却对荣家的振兴,发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人生的机遇,有时纯粹源于偶然。欧阳、韩公云云,则是用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的典故,自比欧阳修,将张之洞比作韩愈了。光绪七年十月,在给吴大澂的另一封信中,张佩纶对胡传再做介绍:胡君传与敝业师夏寿人同在龙门,其去吉林,欲在麾下自效,佩纶未敢力荐,愿私布其下忱,傥可收录,乞即与六厩马群并供驱策耳。夏寿人即夏如椿,为张佩纶早年的老师,后来在龙门书院又与胡传同在刘熙载门下。这恐怕也是张佩纶竭力举荐胡传的另一个原因。张佩纶推荐过的朋友,有的后来与他反目成仇。然而很少往来的胡传,却一直牢记张佩纶对他的帮助,
名正肃就信的内容看,宝廷的儿子也不能劝阻信使递交奏折,张佩纶出于对清流形象的维护考虑,他又退而求其次,指望李鸿藻入朝,“能于明发(上谕)中稍光润些亦好”。斗移星转,二十九日之夜匆匆过去了。除夕之晨,慈禧身体不适,李鸿藻亲临后,军机处代拟了谕旨:宝廷着交部严加议处,即请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仓促之间,也只能这样办理了。张佩纶不知晓军机处内部讨论的细节,故焦虑地向李鸿藻打听情况。同日,他又写一函给李鸿藻,指出:道体已康,甚慰。竹公器小易盈,可为太息痛恨。其意方援子卿胡妇、澹庵黎娃以自解,真谬妄也。圣恩仅予严议,已为宽典矣。朱子诗: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律己观人,又增一重阅历,亦愿公于一二言者,当有听言观行之意,不可再失之于宰予耳。言之闷愧。敬上夫子中堂
佩纶叩上函中子卿即苏武,在匈奴时曾与胡妇生子。澹庵为南宋抗战派名臣胡铨,在被秦桧贬谪岭南后,爱上名叫黎倩的美女。这两个典故,宝廷在自劾的奏折中引用,张佩纶认为谬妄。张佩纶还说,听言观行,不可再失之宰予。宰予是孔子门生,因大白天不读书听讲,躺在床上睡觉,孔子骂他是“朽木不可雕也”。张佩纶与宝廷是好友,此时说出如此尖刻的比喻,足以说明他心中的气恼不悦。这三封密信极为珍贵,捧读原件,我自己似乎也穿越到一百三十年前的那个仓促的夜晚清晨。感受到写信人张佩纶的焦虑不安,更感受到收信人李鸿藻的焦虑不安。此类历史上的密信,本来决不想让外人阅读,能够保存下来,极为难得。张佩纶在急迫之中,字依然写得一丝不乱,也可看出他对李鸿藻的尊敬。十二天后,清廷依部议将宝廷革职。从此宝廷退出政坛,芒鞋竹杖,载酒游山,日以吟咏消遣,最后贫病而卒,成为清流中第一颗陨落的明星。三关于宝廷娶江山船女的故事,野史中多有流传,其前后细节却不清楚。左宗棠年在给徐用仪的信中提道:宝竹坡途次不检,致成笑柄,奉旨切责落职,咎由自取,夫复何言!惟在浙时闻浙人言,前窦东皋先生光鼐视学浙江时,官吏憎其清严,亦曾以船政败其素节。以此知浮名累人,失足即同瓦裂,不容不慎也。竹坡此事先后同符,殊为不值。然自行举发,犹与怙过欺饰者究胜一筹。友朋交谊,应于有过中求无过。信中窦光鼐,为乾隆七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上书房总师傅,曾经三次担任浙江学政。左宗棠所说其“视学浙江时,官吏憎其清严,亦曾以船政败其素节”的内容不详,但左认为窦光鼐是被人做局,而宝廷“此事先后同符,殊为不值”云云,则代表了当年大员中的一种看法。清人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说:宗室竹坡学士宝廷,某科简放福建正考官,复命时驰驿,照例经过浙东一带,地方官备封江山船,送至杭州。此船有桐严妹,年十八,美而慧。宝悦之,夜置千金于船中,挈伎而遁。鸨追至清江,具呈漕督,时漕督某,设席宴宝。乘间以呈纸出示,宝曰,此事无须老兄费心,由弟自行拜折,借用尊印可也。未几奉旨革职。在李伯元笔下,江山船上的特殊服务是浙江官员提供的,这与左宗棠的怀疑相一致。前面提到,宝廷奏折与漕运总督的奏折是由同一位信使送往北京的,信使不敢压下宝廷的奏折,恰好与宝廷要抢在别人举报之前,自行先向皇太后坦白的初衷相符,假若真被李鸿藻、张佩纶派遣的人拦下了,倒是辜负了他谋划自首的一番苦心。此时,漕运总督为满人庆裕,他的弹劾奏折,我迄今尚未见到。宝廷的绯闻曝光后,时任江西学政、远在江西袁州的另一位清流密友陈宝琛十分震惊,二月十二日,他给山西巡抚张之洞写信,希望张能出言上奏,争取为宝廷缓颊复官:去国半年,时局略异,少农罢政,庶子掌台,举错如斯,方惜公与丹公不即柄用,更生乃忽自污,以快谗慝,令人愤懑欲死。谴责固所应得,然其数年来忠谠之言,隐裨朝局,亦中外所知也,当不为一眚所掩。既不蒙曲宥,若久于废弃,恐亦难餍人心。侍与之同年,踪迹又密,欲论其事,则涉阿好党护之嫌,望微言轻,亦恐难回天听。阅钞后,彷徨数昼夜矣,公能为大局一言乎?在渠疏野之性,弃官如屣,方且愎而不悔也。信中更生即西汉人刘向,著名学者,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宣帝、元帝时,因数次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此处借指同为宗室的宝廷。“少农罢政,庶子掌台”,指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王文韶以云南报销案被张佩纶连上三折弹劾,被开缺去职,回籍养亲。同月十一日,张佩纶以右春坊右庶子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与丹公不即柄用”,指光绪七年十一月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和光绪八年初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后尚未得到进一步的使用。光绪前期,清廷中枢由恭亲王奕主持。日常工作,由文祥负责。光绪二年,文祥去世后,两位汉族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李鸿藻承担主要责任。一般认为,沈桂芬本籍江苏吴江,代表南派,李鸿藻籍贯直隶高阳,代表北派。光绪三年九月,李鸿藻丁忧,沈桂芬在很大程度上掌控军机处,并引入同属南派的户部左侍郎王文韶担任军机大臣,互为奥援。六年正月,李鸿藻服阕,重返军机处,以沈桂芬推荐崇厚出使俄国,却在收回伊犁交涉中,划失中国大量利益为契机,组织清议强烈抨击。光绪六年底,沈桂芬去世,李鸿藻在决策中枢的势力大增。用李鸿章的话来概括,就是:“政府周公,久不自专,前唯沈文定之言是听,近则专任高阳”。与他联系紧密的“清流”健将们,一方面更多更猛地参政议政,抨击昏庸腐败大臣,另一方面,李鸿藻也在进行复杂的人事调整布局,包括外派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由张佩纶弹劾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董恂昏庸,将已经退休十余年,隐居山西中条山讲学的前工部右侍郎阎敬铭招入北京,出任户部尚书。张佩纶还弹劾吏部尚书万青藜不孚众望,改由李鸿藻取而代之,控制住官员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的管理权。李鸿章四月因母亲去世丁忧,六月,以朝鲜壬午事变爆发,予以夺情复出以示笼络。当年五六月,宝廷、陈宝琛分别被派任福建、江西乡试正考官,陈宝琛八月还改任江西学政,这些,对这些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的书生型官员,也都是一种经验的历练和丰谀的肥缺。一切正按计划进行,王文韶也逐出了军机处,却忽然传来宝廷的丑闻,陈宝琛顿觉亲痛仇快,“愤懑欲死”,他希望张之洞能为大局发声,如同他俩当年在“庚辰午门案”中的上奏,力挽狂澜。张之洞给陈宝琛的回信我们没有看到过,但我想一定是会有的,将来也许还会被发掘出来。从后续的实际操作来看,张之洞、张佩纶,包括陈宝琛自己,也都没有采取进一步动作。确实,标榜清直正派的士大夫,忽然也来闹绯闻,岂不让所有的朋友都毫无颜面吗?所以,最后“清流”健将们选择了沉默。又过十一年,年,宝廷去世,陈宝琛写《哭竹坡》一诗:大梦先醒弃我归,乍闻除夕泪频挥。隆寒并少青蝇吊,渴葬悬知大鸟飞。千里诀言遗稿在,一秋失悔报书稀。黎涡未算平生误,早羡阳狂是镜机。意思是说,宝廷很早就看出来清流必将衰亡的宿命,携美女退出政坛,不仅不算错误,竟是勘破天机。诗中“黎涡”即酒窝,典出南宋名臣胡铨携黎倩从贬地海南崖州北归途中所写诗句:“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当时对宝廷纳船娘为妾极为不满的张佩纶,后来在《故礼部侍郎宗室竹坡前辈挽词》中也说:使车私买婢,少戆莫交讥。北里聊污韨,南山遂拂衣。先几能脱祸,晚节自知非。社稷忠谋固,桑中罪亦微。陈宝琛、张佩纶写这些诗的时候,清流党已经大败。这些悼念亡友的诗,其实是在感慨故人自我放逐的同时,结合各自命运曲折而发出的喟叹。但到更后来,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竹坡当日以直谏名天下,厥后朝局变,亟以纳江山船妓案自污,遂弃官入山。”一桩不上台面的绯闻,被野史作者看成是深思熟虑后设计的保全自身的政治策略,显然就有点不准确了。四宝廷是以自污的方式急流勇退吗?非也。我从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张佩纶未刊信函中发现,除了前引张佩纶数信之外,光绪九年正月十三日,张佩纶又有致李鸿藻的信,作为重要旁证,可以帮助后人揭破真相:今日过竹公,然而不见。其世兄云,微有悔意,谓负圣母、负公又负二三同人也。对于宝廷不争气,最痛心的,当然是清流自身。弄清真相,也是他们的迫切需要。此信透露,宝廷回京后拒见上门探访的张佩纶,却对儿子流露出几丝后悔,说是对不起慈禧太后、李鸿藻和二三同人。宝廷纳妾,其实就是他不拘小节、放浪形骸的名士做派。宝廷曾作《题焦山文文山墨迹》云:文山歌正气,千秋仰忠烈。闻其未相时,颇不拘小节。始知多情人,乃能有热血。遗迹留名山,墨渖永不灭。意思说文天祥虽然以正气歌千古不朽,但早年私生活也很浪漫多姿。所谓“始知多情人,乃能有热血”,恰是他自己名士心态的真实写照。据说宝廷还作《江山船曲》,有“已将多士收珊纲,何惜中途下玉台?”“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记红裙”、“本来钟鼎若浮云,未必裙钗皆祸水”之诗句,被引用更广的是“江浙衡文眼界宽,两番携妓入长安;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蛾眉不爱官”,流露出宝廷的率真随性,显然未必有更加深刻的谋划。当年,狎妓纳妾是官场的普遍风气,但狎妓又为道德纲常所不许。有学者曾分析说,狎妓的吸引力,也许正在于“不许”。因为“例所不许”,狎妓才会遇到一些周折和意外,这也是狎妓的魅力所在。至于狎妓之后,是否可以化解后遗症,则要看个人官场人脉背景和朝廷政策宽松尺度的掌握。同一件事,有的人干了没事,有的人干了顶多是小节有亏,有的人干了则丢乌纱帽。什么原因?官场机缘加个人运气而已。宝廷被人目为“清流”中的“四谏”之一,一直以清议风骨自许,常常瞄准贪官和庸官撰写弹章,下笔也狠,得罪了不少有头有脸的“粗才俗吏”。报复的目光随时都在搜索证据,此时纳妓为妾,正是授人以柄。作为道德良心的“清流”,恰恰在道德良心上出了问题,轰动效应是可以期待的,革职也是必然的。宝廷纳妾事件,看来是个偶发事件,但在光绪前期政治史上,却是“清流”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值得记录,也值得深入观察。综合各方记载,我们大体知道,宝廷看中的船妓面有麻点,年已二十六七。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刘声木曾记其父听成都将军岐元说:这位如夫人“确曾见过,并无中人之姿,面上且有小痘斑。竹坡眼素短视,又在灯红酒绿之下,看视未真,遽而娶归。以此去官,殊不值也”。李慈铭也作诗嘲讽“江山九姓美人麻”,“侍郎今已婿渔家”。宝廷回京后,“朝论大哗,致侍郎自行检举。朝命未下,寄顿麻美人于客店,不敢即以入府,盖侍郎府第旧王府也”。麻美人姓汪,名檀香,待到风波过去,宝廷遂将其娶入府中。宝廷儿子寿富所编《先考侍郎公年谱》谓:光绪九年正月,公罢职,纳妾汪氏。春游西山,夏游灵光寺,游昆明湖。秋游西山,返宿灵光寺。季子寿康生。寿康是不是汪氏所生,《年谱》没说,这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空间。宝廷敢爱敢恨,弃官如弃屣,虽然对张佩纶说有“悔意”,但依然抱得美人,退隐江湖,可谓大大的名士。宝廷在娶汪氏之前,还另娶李氏、胡氏、盛氏三房姨太太,自谓“余四妾以倩兮、盼兮、悄兮、皎兮分字之”。这些女人,在他罢官之后,并未离他而去,这点使他很引为自豪。也说明他对女人们是很不错的。后世学者有认为他不仅“重色”,而且还很“重情”。五宝廷虽家世显赫,八岁时,其父亲常禄因故革职,不久家道中落,生活极为穷苦。我们常听说前清八旗子弟因不善营生而困顿,却未曾知晓这种穷困潦倒会到什么程度。按照宝廷年谱的记载:当时“室中几案尽售,以砖为座,凭炕而读。积夏苦雨,连日不得食,乃取庭中野菜食之”。宝廷还写过《穷乐府》,其中《无食叹》曰:“朝无食,夕无食,老弱凄凄相对泣。破甑然薪煎菽汁,阿爷凄惶面菜色。阿爷养我时,膏粱酒肉无时亏。”《无火叹》曰:“炉无火,委席左,父子缩首迎阳坐。朝阳微微无暖气,老父今年六十二。”他说,所言皆己事,不兼以他人。宝廷29岁考中进士,因敢于言事而颇得圣眷。同光年间,战乱初平,国家积贫积弱,外侮日深。朝中却是文恬武嬉,不思危机将至。此时,一批敢言的文官拍案而起,在军机大臣李鸿藻的暗中支持下,论政建言、弹劾贪腐,逐渐形成强大的被称作“清流”的政治势力,宝廷正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而他本人,不过十四年工夫,已经做到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和礼部右侍郎。罢官之后,宝廷流连京郊景色,写了大量诗歌,被认为是有清一代最大的满族诗人,可与康熙年间满族第一词人纳兰性德相比肩。他筑室西山,间往居之。樵夫牧竖,久之皆相识,却不知其曾为卿贰。宝廷失去俸禄后,生活再陷贫困,客至,常不能具酒食。朋友周济的金钱,到手即沽饮,或赠更贫者。宝廷曾在西山八大处的灵光寺题壁:壮志豪情一律删,怡然终日总欢颜。攀岩自诩身犹健,照水方知鬓已斑。世上难沽常醉酒,人生能得几年闲?迩来尽享无官福,四月之中四入山。当时,门生郑孝胥曾去西山看他,留下《怀座主宝竹坡侍郎坡》的诗篇,既是对宝廷西山隐居生活的写照,也是对其生活作风错误的惋惜:沧海门生来一见,侍郎憔悴掩柴扉。休官竟以诗人老,祈死方知国事非。小节蹉跎公可惜,同朝名德世多讥。西山终岁勤还往,愁绝残阳挂翠微。再后来,张佩纶马江兵败,遣戍张家口,光绪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年4月19日)到达北京。二十日,宝廷与张佩纶见面,作《立夏前一日送张幼樵之军台》:忆昔从班,联步趋彤廷。簪毫效献替,求应同气声。狂奴自不靖,败裂嗟声名。累公独报国,夙夜殚忠贞。岂期命途舛,志大功难成。荷戈远戍边,万里西北行。…………圣朝开言路,讲幄有四友。忽忽六年间,凋零怯回首。何逊死扬州,全终名不朽。叔度倖贵显,在外已成叟。公虽得奇祸,天数亦非偶。功过公论在,何劳强分剖。贱子独不材,休官罪自取。补赎叹无从,天恩负高厚。养拙甘长终,思归田无有。未老难遽死,苟活焉耐久。时艰国易误,累重贫难守。无聊惟自促,妇人复醇酒。忧辱脱生前,褒诛听死后。了此无用身,庶免增戾咎。…………豪杰喜骂人,得祸此居半。势盛隐衔恨,时失显罹患。纵使幸免祸,亦愧非本分。学问与涵养,于此胥可见。我生夙躁率,狂言每招怨。穷途益不平,使酒增愤愤。故友知我病,苦口屡规劝。持此转语公,幸勿言河汉。送君出塞行,花下同倾杯。可怜两枝花,尽被东风催。一枝花坠地,一枝随风飞。回思花始盛,曾赖风吹开。东皇岂有心,物候应天时。把酒送公去,正值春将归。春归明年还,公去何时回?诗中叔度、何逊指清流健将张之洞、何金寿。何金寿光绪八年七月死于扬州知府任上。全诗是对清流由勃兴到衰灭的回顾。宝廷说:“圣朝开言路,讲幄有四友。忽忽六年间,凋零怯回首。”“豪杰喜骂人,得祸此居半。势盛隐衔恨,时失显罹患。”“送君出塞行,花下同倾杯。可怜两枝花,尽被东风催。”到了失意的时候,大家更感到当年的豪情和搏击,不过如一场春梦。“回思花始盛,曾赖风吹开。东皇岂有心,物候应天时。”他们曾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又是政治操纵者的工具,等到看清这一点,他们也悄然退出了政治舞台。这年六月二十七日(8月7日),翁同龢游西山八大处,看到了宝廷的题诗,亦题一首,补于壁后:衮衮中朝彦,何人第一流?苍茫万言疏,悱恻五湖舟。直谏吾终敬,长贫尔岂愁。何时枫叶下,同醉万山秋。显然,翁同龢对宝廷的际遇还是满怀同情的。宝廷对于自己的放浪形骸却有后悔。光绪十四年秋,长子寿富中举,他作诗云:老病疏家教,惭闻子举乡。国恩今始受,父过汝休忘。海内乾坤仄,人生岁月忙。诗书希有用,干蛊岂文章。诗中,他对儿子提到“父过汝休忘”,在另一首诗中,他甚至提到“吾过赖汝补”。这里已没有名士的矫情,流露的是一个失意的父亲对儿子成长的期望。费行简曾记载:“予后见(宝廷)于京师剧馆中,已憔悴,霜雪盈颠矣。然尤娓娓道其近作。已而同入酒家,饮亦尽十余斗。后闻其中酒卧道中,冒寒归,竟病卒。其妾楚楚有林下风,侍廷尤勤恳,先死。”而按照寿富所编《先考侍郎公年谱》的说法,宝廷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年12月24日)因感染瘟疫而去世,与过度饮酒无关。宝廷的季子寿康三岁亡故。另外两个儿子寿富和富寿,娶了联元的两个女儿为妻。联元,满洲镶红旗人,字仙蘅,与宝廷是同治戊辰科进士同年。光绪二十四年,擢安徽按察使,入觐,改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年,授太常寺卿,旋改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衔。义和团运动兴起,在朝廷御前大臣会议上,联元反对围攻各国使馆,与慈禧太后旨意相忤,以“任意妄奏,语涉离间”罪名,与徐用仪、立山等同时被杀于北京。不久,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寿富、富寿及妹妹隽如、淑如不愿受辱,举家自杀殉难,死事十分惨烈。又越十年,宝廷在福建典乡试所录门生林纾,亦在西山看到宝廷的题壁诗,遂也题诗:题名忽及偶斋师,竟似重生再见期。八口宁忘泉下痛,(师二子于庚子殉节,四孙去年同以疫死)廿年犹泚壁间诗。料无风概宗先辈,忍对沧桑语感时。(弢庵为余述光绪辛 巳壬午朝事甚悉)早晚商量校遣草,门生也感鬓边丝。此时,大清王朝已经走到行将灭亡的前夜了。年5月初稿年2月修订年7月再次修订书虫子
|
时间:2021/4/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牡丹江市公路客运总站年春节期间发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