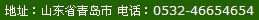|
1 年,我在大哥的引领下走进了村西大庙。西大庙是我们村的学校。在后院大厅旁昏暗的西角殿里,我坐在一个更加昏暗的角落里,乌泱泱的孩子们在我额前晃动,感觉自己像掉进了无底深渊。 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毛主席万岁!我认识那几个字,因为我们家墙壁上一直挂着毛主席像,下面就是那几个字。 一位姓申的中年女老师在我们中间游弋着,在密集的桌凳和人头间巡睃着,轻松自在,宛如一尾在珊瑚礁中灵活自如的大鱼。 我左边的女孩子“吧嗒吧嗒”掉眼泪,手紧紧攥着笔,仿佛担心笔会被人拔走似的。右边的男孩子咬铅笔头,一眼一眼看我。 到了三年级,我们从昏暗的角殿搬进了宽敞的大厅。大厅大且高,让我觉得自己更加渺小了。在大厅一直读完了四年级。大厅后坡的屋顶东西塌了两只大窟窿,夏天塌了一只,雨往里灌,冬天又塌了一只,雪往里飘。两只窟窿像两只巨大的眼睛,我盯着它们看,它们也盯着我看。冬天塌的那一只,塌得不利落,有两根一米多长的椽耷拉着,却没有掉下,风钻窟窿,跟着风来回晃悠。彼时,姓申的女老师已经不常来给我们上课了,据说她有病,什么病我们都不知道。实际上从二年级开始,她就没好好上过课,我们的教室总是像羊群一样乱,到了大厅,地方宽敞,就更乱了。 校长姓崔,名字里有个“笑”字,脸却不带笑,习惯用阴鸷的眼睛歪着脖子剜看我们。他抽旱烟,烟袋很讲究,一管巴掌长烟袋两头用黄铜包了,头前是蛤蟆皮,后头烟嘴儿像个金灿灿的花瓶。他种菜地,在庙门外西边的围墙前,一大块。我们胆敢到菜地里玩儿,捉住那是不得了的。我还见过他捉了一窝没有出窝的小老鼠,姆指肚大小,有四五个吧?他用细线挨个拴了尾巴,提溜着一下一下放在煤油灯头上烧,这些粉红色的肉球球一近火头,会发出极细的怪叫声。他后来不知在哪搞了一大捆麦子,到村第一生产小队的打麦场上用打麦机脱粒,不慎引发火灾,把生产队一场麦子烧毁了。 我们乱得实在过分了,影响到其它班级上课,他就出现了,大厅的木隔扇门窗非常高大,他圆圆的脑袋矮矮地伸进来,得意忘形的我们一片惊慌,桌翻凳倒中我们各自迅速归位。他站在讲台上,等尘埃落定,总能准确地揪出几个带头的,赏每人几个响亮耳光。他不管我们文化课,只教我们唱歌,什么《学习雷锋好榜样》啦,《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啦等等。 申老师偶尔也会出现在讲台上,尽管她就是我们村人。她性子很急,恨铁不成钢,总嫌我们领悟课本慢。她骂我们时总是提到我,几乎成了口头禅:“张军利,还有那个谁谁谁,一二年级的时候可都是顶呱呱的把式,现在呢?”她用手背狠狠磕击桌面,“现在呢?都是大鸡蛋呀!零蛋蛋呀!”她把重音压在“呀”字上,声音高低起伏,抑扬顿挫,痛惜之情今天还在我眼前活灵活现。某一次放学后,她把我带到她家里,一边忙着捅火、坐锅、添水,一边教育傻乎乎站在一旁的我。她简直是语重心长了,她说:“孩儿呀,聪明明儿一个孩儿,浓眉大眼虎头虎脑,怎么就不知道学习哩!不学上本事将来长大了做什么?”她迟疑一下,“——只能像农民伯伯一样担茅粪!你想长大了想担茅粪?——告诉我,想不想?”我嗓子发痒咳了一声,那声音在她听来变成了十分肯定的答复,她闻之大怒,舞着两只面手把我撵出了家门。出得门来我并未多想,及时回家吃饭是一种幸福,因为每顿饭汤汤水水,到了顿头总是饿得发慌。后来她在课堂上讥讽我是担茅能手,我虽感委屈但仍不当回事——她耳朵真不好使,我才没有答应担茅哩!那时候孩子们没甚心机,哄堂大笑过后,再没人提起,大家照样可着命玩儿。但是没过几天我遭了父亲一顿暴打,原因是我做错了事,而父亲又恰巧刚从她口里听闻了我的担茅之能和顽劣不教。 五六年级我们搬到了大庙西侧的平房里,还在后半院。实际上这个时候,学校所有屋顶我都爬过无数次了,包括大厅前的雕花斗拱。支撑斗拱的横梁下面石柱顶着,横梁上挂着敲响我们上学放学的大铁钟,大铁钟的边沿有一个拳头大小的豁口,但声音依旧雄浑厚重余音悠长。敲钟的长绳拴在大厅前左侧第一根石柱上,“一上二下三准备”,我们学生都知道要领,老师一指谁,谁就抢着去敲,我也因此常常成为一个敲响钟声的人。 有一次钻斗拱,骑在横梁上,用脚蹬敲钟的铁槌,够不着,努力往下侧身,不想弄出了“当当”两声,虽然是星期天,寂静一片,学校却是有驻校老师的,吓得赶紧抽身撤离,猴子一样缩成一团,躲在斗拱缝隙里一动不动。果然有老师前来察看,背着手抬着头转圈盯看,仿佛不解因何无故自鸣——实际上他心里是有数的,故意不揭穿,让捣乱的人在上面憋着。 我一般从学校东角殿围墙外的一棵歪脖树上爬进爬出,现在这棵树不知何故砍了,树桩还在,糟朽得不成样子了。西角殿台阶下的围墙边也有一棵细小的槐树,长在水泵房的窗前(记不清什么时间,西角殿台阶下的围墙扒开了一个口,占校园地面修成了大队社员看水泵的房子)。有一次从水泵房瓦顶顺着小槐树下来,到各年级教室捣乱了一番,想再顺着爬上去溜掉时却发现特别不容易,因为小槐树离水泵房瓦顶和围墙都有一臂长距离,好不容易爬上去,脚刚好够着围墙或瓦顶,那小树就往里边倒,晃晃悠悠,很难得逞。好在那个星期天驻校老师都不在,后来我再不敢顺着小槐树溜进校园了。 还是在小槐树旁,有一次同学之间打架,一个同学被打倒,躺在小槐树下没气了,我们所有围观的同学开始兴奋地大叫:“出人民事了!出人民事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命关天这些道理,命民不分,但跟着叫得起劲。人多力量大,在我们震天的叫喊声中,那位同学又“呼哧呼哧”喘起来了,“人民事”最终啥事也没有了,我幼小的心灵不免有些淡淡的失落。 我上初二的时候,二叔在水泵房看水泵。有一天,我站到了水泵房的窗台上,顺着窗户的缝隙往里看,他不在里面,在挨墙角一块脏兮兮的铺板上,我突然看到了我在南村百货商店新华书店柜台上买的《赵树理小说选》,它被随意扔在上面,几根谷秆压在封面上。天!他大字不识几个,却装模作样看书!那一刻,我恨透了二叔。这本书后来再也没有回到我手中。 同样令我气愤的是,我上初中后订过一年《汾水》杂志,我精心保存的杂志,在我初中毕业后不久的某一天突然出现在我大舅家低矮的厨房的瓦棱间。当时,我大舅家正修房子,我在那儿当小工,前夜的一场雨已经把它们淋成了软塌塌的一大坨! 这两件痛彻少年心扉的往事我从未向任何人讲起,少年的我似乎没有任何诉说和抗争的权利,如果那样做了,父母可能只会嫌烦和无故恼怒,我默默吞下了这两枚难以下咽的果子。 我何至于有钱买回那本《赵树理小说选》?我想唯一的可能是父亲给予我的奖赏,我学习有所进步——初一期末我领回了一张“三好学生”奖状。这是我当学生期间第一次领奖状,也是最后一次。 说不清什么原因,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到南村百货商场的新华书店柜台前转悠。柜台上书不多,记得有孙犁的《铁木前传》,郭澄清的《大刀记》,胡正的《汾水长流》,还有一本《烽火岁月》,一本《黑奴吁天录》等。粉碎“四人帮”后,柜台上高高挂起了四个竖条幅,红底黑字,上书郭沫若《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上阕:“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大条幅把柜台后面的东西全遮住了。 我73年上学,76年粉碎“四人帮”,算起来无非升到小学四年级,但是我总觉得粉碎“四人帮”是我升了五六年级以后的事。有一次政治考试,有一道题叫“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答得简单:“像英明领袖华主席一样,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 我们初中的班主任老师姓贺。 初一时,贺老师鼓励学生订杂志,少数几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订了《少年文艺》《儿童时代》和一本什么画报的,我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订了《汾水》。也不完全是农民家庭,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到公社的农科站了,虽然身份还是农民,却已经成了拿工资的人。 我之所以订《汾水》是因为我知道它是山西最高的文学刊物,它的前身叫《火花》,我已经在《火花》上读过好几篇有趣的小说了。我们生产队有个木匠,他有厚厚一大本《火花》,好多期订在一起,轻易不示人,借给我父亲看时,所以我有幸看到了。 如果说那时候我开始喜欢读书,也未尽然,因为到现在我也不敢说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我只是喜欢热闹,一目十行地胡乱翻,一知半解就扔一边了。仔细想来,养成我这种坏习惯的,是我们家里不缺书。我父亲是原晋城农校的高材生,他是很爱惜书的。我们家里有绣像版繁体竖排的《三国演义》,有《东周列国志》《镜花缘》《啼笑因缘》《封神榜》《千家诗》《中国近代史》《宋词选注》《易经》等等,书虽不多且乱,但确实够我平时翻翻的。 叫我涕泗横流的一本书没有名字,前面短了差不多三十多个页码,后面短的更多,纸质发黄,只能叫半本,我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摸出来的,讲一户人家一路逃荒到了阳泉,后在日本人管制的煤矿下窑讨生活,日本人如何压榨和毒打工人,这家人最后死的只剩下一个九岁小男孩,小男孩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父母的死尸再无下文的故事。我在柴油灯下读(村里有装柴油的油罐,家家都托人弄回柴油来点灯,省煤油钱),饭也没吃,两只鼻孔熏得第二天掏还是黑的,眼泪鼻涕摸糊了一身。 再一本叫我神迷的是《西游记》。小时候父亲给我讲过其中一些故事,虽然也是缺头少尾的半本书,可能还是简写本,但我看了几眼即知道它是《西游记》。书是大哥从怀里掏出来的。父亲命大哥领着我到半人高的玉米地里拔草(生产队分给各户的任务),刚钻进地里,大哥就掏出来了。我们共同看了几页后,就开始争抢,最后大哥把书扔给了我,我下午一棵草没拔,看完了那半本书。 还有两本书印象深刻。一是《大刀记》。《大刀记》是通读了一遍的。星期天,院里大人都上地了,我一个人坐在我家堂屋的窗台上看,背靠着墙,双腿长长展开,太阳暖暖照着,很舒服。有一章叫“重返宁安寨”,主人公的大智大勇临危不惧让我血脉贲张,胳膊腿跟着主人公一起张扬,一不小心从窗台上重重地摔了下来。 再一本书叫《雁翎游击队》,借同学的,看了几十页,同学收走了。看这本书,发现了小说写作的一个秘密:原来写一个人此时此刻干什么,过一会还可以写另一个人也在这个时间段内干什么,小说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一样,可以有好多个头啊! 还读过刘心武的《班主任》。《班主任》轰动一时,名噪全国,不好看。 还读过卢新华的《伤痕》。读《伤痕》时我可能已经初中毕业了。《伤痕》是一个爱情故事,好看。读郑义的《枫》,我确定已经离开学校开始喂牲口了。 我们那一届学生例外,初中三年(我们以前的初中是二年制,我们之后有一段时间初中也是二年制),所以,加小学五年,我一共读了八年书。 初中毕业前最后那一个月,我们班四十八名同学,留下来复习准备考高中的一半不到了,因为那一年土地下放了,家长和部分同学早不安心在学校继续“耽搁”下去了。 复习期间,我带了一本厚厚的《三侠五义》。数学老师在讲台上讲,我低着头看书,看到入神,忘了防备。数学老走到我跟前说:“嗬,够厚呀!”数学老师没收了书,一个月后又把书原封不动还给了我,但他当时把状告到了我父亲那里。 数学老师初二时还关过我禁闭,他上课时我不准进教室——他总是预先把我锁在他的单间宿舍里,锁了整整一个多月。这中间,我被锁得不耐烦,在门后用粉笔头写了“拘留所”三个字,写过不放心,抬起袖擦了,断不知他眼尖得要命,没隔半天就发现和辨别出了那三个字,对我实施了好生一顿痛揍。 他住东边的教师宿舍。东边的宿舍和西边的教室不一样,门外有一条两米宽走廊,下三四个台阶,才是校园的大院子。 有一次我和同桌在校园外水泵房前的水池里扔石头,被他捉住了,他把我们带回宿舍训斥。他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破坏水利设施就是现行反革命,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说知道。他说知道就好,摆摆手让我们回教室。刚到外面走廊上,同桌不知何故,学起了电影《小兵张嘎》中的翻译官:“哼哼!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掏钱,慢说两个烂西瓜!”话音未落,就觉得身后一团黑影闪出,“嗵”的一声,同桌像烂纸片一样已经飞到了大院子正中,我吓得没命狂奔,一股劲冲出了校门。回头看,同桌在院子当中早被数学老师打了个七荤八素。后来数学老师在讲台上说,个别同学可恶到了极点,什么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掏钱,是不是说老子干了多少坏事都不说,慢说在水池子里扔了几块大石头? 数学老师除打人利索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语文,数学,历史,地理都通;英语出去培训了一周,回来就开始教我们;体育也行,篮球乒乓球打得都漂亮;音乐也厉害,脚踏风琴,手风琴,二胡,小号都会弹会拉会吹。他是民办教员,后来转正了。他还是个酒鬼,我长大后,和他在一起没少喝酒。前几年他去世前我们还喝了一场酒,酒后他就住院了,回来后,我去看他,他说:“医院,一个咳嗽也治不好。”他得的是肺癌,话说过没几天,就去世了。 我自然没有考上高中。考物理时睡着了,口水洇湿了试卷一大片,监考老师叫醒我:“你睡没人管你,你不能打呼噜影响其他同学。去,到门口把卷纸晒晒吧。”我当然没有丢人现眼去晒卷纸。 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了,它始于村西大庙止于村西大庙,也算善始善终吧。 2我开始喂养一头骡子。 土地下放,我们家分得一头高大威猛的骡子。我家的骡子叫大骡,它后面还有二骡三骡,二骡三骡分给了其他两家。二骡是一头母骡子,骨骼奇崛,皮毛光亮,禇红色,大我家骡子一圈儿。初中课本《暴风骤雨》中节选的课文《分马》,那匹栗色的小耳马可是比不上这头骡子,但它是骡子不是马,假如是马,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三骡还没调教出来,青口,不会拉车犁地,后来我和他家的小儿子调教的。三头骡子并排站在饲养处的一溜槽前吃草,但是各家喂养各家。骡子吃过草,剩下的草圪节拌料——就是洒上水,撒几把麸皮,用棍子搅匀。草圪节沾上麸皮,骡子吃得起劲。拌料时,我需要小心,因为稍不注意,二骡和三骡就会拉长缰绳伸头过来偷吃几嘴。后来我们在饲养处里打了几堵墙,我家骡子和三骡占了三间屋,两头骡子一边一个,槽分开,中间留过道,就不存在谁家牲口偷吃谁家的料了。 父亲在槽前给我搭了一个空中铺子,方便半夜给骡子添草,“马无夜草不肥”么。但我好像在上面没睡几回。 星期天父亲和我给骡子铡草,在饲养处上面的打麦场上,我们占了一间庵子,铡一庵子的谷草,够骡子吃半个月的。 喂养三骡的是我们生产队的老饲养员,他拐了一条腿,记事起,他就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他家的小孩子和我同班,比我大两岁,但更加淘气,不舍得掏力气干活儿,他拐着条腿逮不着他,只好求我。铡草,他坐在下边往刀口送草,我站着握着刀把儿往下压。给我家铡时草不能长过一寸,给他家铡时短了两寸我不允,弄得老头儿没办法,只得听我。我每天给骡子担水,他家三天也没人担一担,他也只好求我,我家骡子喝剩下他家骡子才能喝上。我出槽后勤,他家槽后和砂石槽平了也没人出,三骡像住在楼上,撅着屁股艰难地低头吃草,怪可怜也怪有意思的。 邻村西峪天天晚上放电影,浪井村有时也放。晚上看电影回来我去给骡子添草,老饲养员如果没睡,一般要我留下和他说会闲话。因为孩子多,家里没地方,老饲养员睡在三骡槽前的砖炕上。听着骡子嚼草的声音,闻着槽后味儿,我大多会留下(好几年前,在白马寺绿苑的一次文化沙龙上,我还深情回忆了一番槽后味儿如何好闻,引得男同胞大惑不解,女同胞花容失色)。他知道的水浒故事多,三国少,我不和他聊水浒,专聊三国。讲失街亭时,我一口一个马骡(谡),讲得唾沫横飞,他一句话也插不上。 老饲养员一辈子没有剪过脚趾甲;没刮过胡子,长了用一把锈剪绞,绞得参差不齐像狗啃过;他们家祖传给牲口治病,传到他这一代,大概失传了,但还有人找他给牲口看病,我和他去给一匹马看过,他说马感冒了,笼头吊起马头,在马的耳朵上“咔咔”两剪,绞了三角口子,用的就是那把锈剪;他不识字,却也喜欢附庸风雅,常给我吟诵“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样的句子。 老饲养员见过几次赵树理,和赵树理并排坐在浪井村的舞台下看过戏,知道赵树理是大作家,所以特别爱向我讲赵树理。“赵树理,那可是大人物,天下第一大才子,写的书没有人不看的,中国人看外国人也看!”我问:“你看过?”他说:“当然看过呀!小二黑……”我打断他:“你不识字怎么看?”他说:“不识字也能看小二黑!”看着我不屑,他就又重复起和我说过一百遍的话:“我和赵树理坐在一起看过戏,在浪井村,赵树理戴一顶黑呢子帽,赵树理吸我的旱烟,给我吸他的纸烟,纸烟哦……”我说:“你不吸烟怎么让吸你的旱烟?”他说:“我现在不吸了,那时候吸!” ………… 骡子喂了一年多不到两年,父亲把骡卖了。 骡马驴是高脚,除了打滚儿,和牛不同,是从来不卧的,白天黑夜一直站着。我的骡后来夜里经常卧下,白天站不起来,我打它,它也只能勉强站起两条前腿来,后腿无论怎样用力也站不起来,眼看着快起来了总是轰一下塌下去。我叫来人抬它,肚下穿一条宽带子,两人往起抬,后面再有一个人拽尾巴,三人齐心协力,连吆喝带抬,它才能起来。站起来还能拉车干活。“马瘦毛长”,我赶着骡车一晃一晃走在街上,路过饭场,喂养二骡的那家老头儿笑话我,说:“呦,看把大骡喂成甚了,长翅膀了,一会就飞天上了!”他家二骡毛光水色,村里人都说喂得好。我生气,把骡车往路旁的杨树上一拴,扑过去和他打架。 骡子喂成这般光景,我也心疼,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确实是悉心喂养它的。它左侧的一根肋骨折了,这条肋骨比它整排肋骨低了一寸多,不用摸,肉眼就能看见。老饲养员说,是当年队里调教牲口的人打折的。它卧下起不来前,我在槽里发现它脱落了三颗大牙齿,每颗都比红枣大,蛀虫蚀空了。 父亲从未和我说过要卖掉骡子,那天我不在家,回来后去喂骡子,槽后空空荡荡,三骡在一边四蹄乱踢踏,不断朝我“咴咴”叫,我预感不祥,一问,才知道被父亲卖给了南边一个老头子,离我家很远很远,快到河南了。骡子走时披挂整齐,套了它拉的车,车上装着它拉的犁,走得干干净净。我在夜里哭醒了,狠劲吸溜鼻子,鼻子吸酸了,也闻不到它身上一丝儿的汗腥味儿了。它是真的走了,走得干干净净。 我很伤心!到现在也不太想回忆它的样子,尤其是它的眼神。 晋城文化界某名士开了一家小面馆,某次我到那儿吃面,赫然看见面馆的墙壁上挂着牲口拉车用的全部物件,围脖啊,夹板啊,小鞍啊,三角啊,坐秋啊什么的,我的泪就忍不住下来了,我知道骡子已经融进我的血液里了。 我也清楚它早不在世间了——因为它走时已经是头老骡了。我不知道它后来的主人是把它掩埋了还是弃置荒野而不顾——任其在太行山的山石间腐烂,腐肉被食腐动物和苍蝇围攻,骨头被风吹得七零八落。 我把怀念和担心写成了一首小诗,某一日发神经,曾面向它离我而去的方向吟诵不止且泪雨滂沱。 生活就是这样,得失之间,我慢慢长大了。这一段生活经历,给我后来写文字留下了巨大的可不断挖掘的矿藏。我的散文《套相》《摩托·骡车》《昨夜大雪路》,小说《春风怨》《大宅院》,还有不少诗歌,都和这段生活有关。 昨天和弟妹们在
|
时间:2021/9/1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宁夏国企学校医院都在招聘,正在报名,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