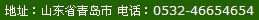|
家乡"水胡基“小记(散文) 作者王顺利散文(原创) 乡愁,是一条割不断的红丝线,走到千里之外依然魂牵梦萦,割舍不下。一件过去普通得就象流过一次汗,而这流汗是千万次中也是最平常的一次,但在岁月的过滤中还清晰地记得,刻在心上难以忘怀。这乡愁,大得如一座山,谁也拖不走,小得如一节家乡荷塘的莲藕,吃一口清脆香甜的味道能记一辈子。就拿看似是农村一件小事,却又是每户居家的大事,比如做"水胡基“,在陕南汉中乡下农村,它是成千上万种农事的一种。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也许比民国还早许多,司空见惯的盖房,撘牛棚,垒猪圈,砌羊圈,灶台,茅厕等,就是用"水胡基“干坯来完成的。在寸土如金我的家乡,一马平川的田块一年两季收成,即五月中旬收麦,十一月中旬收稻,沒有半寸闲置的地块。在平地起房造屋的祖辈们,抱着对生活更理想化,居住更牢固化的願望,用现今流行语说,激发聪明才智,广纳奇招妙想,在不占一分农田的情况下,在田埂,沟渠,泥塘,因地制宜就取材地,制做"水胡基",成为乡下人家垒墙最基础的材料。传说,称为"水胡基"的土坯,为鲁班技艺所创。在陕西,因地理环境旳不同,"水胡基"多见于陕南汉中地区,水为媒介。而"旱胡基"则见于关中地区,以干为特征。人们把胡基归于鲁班发明,想必是做胡基的工具是木制的,故首推木匠的祖师爷鲁班。我们不探究其渊源,只欣慰先祖给后人提供了改变居住条件的钥匙。很久以前陕南农村的农民栖息始于人字架搭草帘,陋居窝棚,用胡基垒墙建屋后,什至到能挡风遮雨称之为"房",从质上是一个飞跃。"水胡基“,它制做方法说简单也复杂,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说简单农村的男劳力都能胜任,说复杂是自开始到制做完成归位时间达几月,要经过多道工序。每年六,七月,家乡稻田的田埂边,水渠傍,泥塘沿,无名的野草得益于雨水的充分滋养,远远望去,象一条条绿色的缎带伸向四面八方。需求"水胡基"的农户乘光照充足,日照长的时光,亊先选好自己中意的一,两处地段,扛起锄头,铁铣,把上面的杂草连土锄起,铲进水沟里,天热杂草混合泥块在水里发酵快,半个月二十天后叶子腐烂,根,筋混在泥水里,算是泡到火侯。这时,赶早上好太阳,拿上做"水胡基"的模具,先将一段田埂平整好,摆平放正模具,它是一个能开合的长方形木框,约十公分高,一尺宽,尺二长。一人站在高处,弯腰使劲用锄头上下左右来回将泥带草筋翻动,软硬适中后,模框上均匀浸湿水,一锄头一锄头捞起填入,至木模填满,一人紧跟其后,做扫尾修整,哪儿少点不平添上一锄半锄,再用锄头沾水抹平搪光,后双手轻轻托平将模具提出,表面光滑整齐的一块水胡基算大功告成。再将脚下散落的泥草铲净,脚下利索为止,以秩类推继续。至止吃午饭,一晌下来,壮劳力也就能托坯百十块,已是大汗淋淋腰酸背困。抬起酸楚的腰,手搭凉棚,看着一字摆开,几十块在阳光下如镜面般光洁的水胡基,累也就不在话下。为防止雨淋,用稻草覆在面上。如太阳持续看好,十天半个月后,把它们以秩翻起,再凉晒些日头就可以或人抬,或用架子车拉回。晒干后的水胡基每块重三四十斤,那时侯,沒有什么运输机械,全凭人抬肩扛,架子车全村就那么两三把,所以,主要还是人抬。两人用木板托底栓上绳索一次抬四五块,回家垒整齐置放在房前屋后通风处,搭上草帘,这仅是一次的。盖房备料,看每个家庭的情况,有无时间,劳力多少,天气晴好等,多者一年夏秋季能托坯做水胡基十次二十次,几千块,少者就无定论。要盖三间房,就得三五年备料。从前家乡人盖房,光景好的房子是"硬列子“,即房子的顶柱,大梁,横梁搭好骨架,再用水胡基垒墙,这就是农村人说的"墙倒房不倒“。水胡基里加杂有草根,筋,同现在的水泥板中加入钢筋一般,提高了抗拉抗压承载力。"硬列子“加上"水胡基",墙面被泥水匠用稻壳裏泥压平搪光粉饰,光滑美观又增强了保暖,但更重要的是墙体的强度提高了。一座看似其貌不扬,却沾着地气,土气且结实耐用的房子,历经百年风吹雨淋不倒。如果你现在行走于汉中乡村背巷,碰巧还能在一隅觅到一栋两栋,那苍老却依旧健在的老宅。居住几十年后,外墙因长年蜜蜂成群坐窝钻洞,墙体四周成了麻脸婆,有邻家或亲朋好友找上门来,会主动替你拆旧墙,重新换上新墙。你道为何?原来旧墙的土坯纳风霜烈日几十载,吸天地精华滋养,是除了农家肥之外上地的最好肥料,对改善庄稼地营养结构有持续后劲。祖辈们世世代代跟土地打交道,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生产生活技能,这便是其中之一。要不,谁也不会干拆了东墙补西墙的蠢事。"水胡基”,因势而产生于陕南汉中水乡。与之相对应的"旱胡基“则在与秦岭相隔的关中平原。用途一样,制做方法除模具大同小异外,托坯制做上有别。做"旱胡基“,首先要选上好的黄粘土,干湿适中,以抓一把攒在手心张开不散为宜。底座垫一块平整光滑石板,木模放平,框内均匀撒上草木灰便于翻动。填满土,用双脚四下踩实,双臂高高抬起石锤手柄,落下狠狠砸在正中,再前后左右开弓,重复几次,后用脚趟平胡基表面浮土,随后蹬开木模开合机关,放置一边,两手分左右轻轻托起,一块成形的旱胡基算是制做完成,后以秩排列垒放整齐。身居秦岭南北的乡亲,祖祖辈辈在农村这块土地上,生与斯,长与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用智慧和一双勤劳的双手,解决了盖房的最基本建材,从根本上改变了居住生存环境,成为遵循自然发展规律,不断探索发明创造的受益者。我时常联想到现在的生活,逐景生情,游历在过去的时光里,岁月的长廊里留下许多印记。故乡从前的一人一物,一哭一笑,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亲眼见过的,听人讲述的,它似划痕深深刻在脑海里。那时的邻里乡亲,冬天,吃饭蹲在朝阳背风的房檐下,说着奇闻轶亊,讲春种夏收,諞农耕技艺,清苦中有一种洒脱,平淡,安稳。邻家有事,隔院墙喊一声马上就有人过来相帮。盖房造屋,婚丧嫁娶,家中添丁加口,全村老少出动,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主动相帮成了那时人埋在心里的潜意识。清晨,丝丝细雨,枭枭炊烟从房顶瓦的缝隙里什腾飘向空中,与远处的岚山交汇在一起时隐时现,分割成不同网格状的稻田,青翠的秧苗披上薄如蝉翼的轻纱,虚雾飘渺中呈现田园风光的诗意美,胧朦美。晌午,有孩童放学未进家门。童音便钻进屋内:"妈妈,我回来了!“接着,是妈妈在屋内忙碌丢出来的一声"狗娃子,快到圈里给猪娃儿添瓢糠,一早还沒顾上喂它呢。“傍晚,女主人大声喊碎娃回家的,吆喝鸡上架的声音此起彼伏。夜晚,村上老少爷们,大嬸小姨拿上蒲扇,端上木櫈,谈天说地到麦场看电影嘻笑的欢快声。还有那河里捕鱼,上树捕鸟,稻田捉黄鳝,滚铁环,儿少时玩得不亦乐乎的天真无邪。最不能忘怀的,小弟弟,小妹妹们追逐打闹捉迷藏,玩老鹰抓小鸡,丟沙包,捉蛐蛐时的呐喊声。晨曦中,远处不时传来几声公鸡的啼鸣,瞬间,引来远处狗叫的吠声,乡村祥和,安宁,淡恬的景色多么象一幅素雅的民俗风情画。想着它,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甜美成了对过去生活的一种深深眷恋。现今,胡基在乡下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成为历史。久居城里的我,梦里时常浮现从前在乡下的生活,仿佛又闻到老屋墙壁沾着泥土的芳香,听见清晨鸡鸣的啼声,又见老农手扶犁把黄牛耕地在田间,心就落在实处,象一只返巢的家雁有了归宿感。现代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缩短了时间,坐地日行八万里已不是空话。我赞叹社会旳文明进步,工业化,自动化,信息化,城市化正飞速发展,改变着这个社会的进程。同时,心里却平添一缕千人一面,程序化引起的思想困惑。走到哪里,都有曾相识的面孔,但又是那般莫生,城市火柴盒式的高楼大厦很象是立着的高高低低的积木,雷同,单调,缺了地域,人文的个性张扬。留心看一些城市街道两傍,商铺门头简单化一,说黄色一街两行穿越几百米绝无二色。曾几何时,城市商铺门头牌匾制做的材质各取所好,形状各有千秋,字有大小,色有不同,牌匾所写,所刻的字体集书法之大成,浓浓墨香味沁人心脾,潜移默化中受益于文化氛围的熏陶。现今变成了一样的双胞胎,看不见柳,颜,找不着楷,隶。挤兑了大脑储存记忆的空间,留给我们能回味的东西越来越少。流淌的悠悠岁月,漂白了两鬓银发。过滤下那些记忆中珍藏的往事,它们也许不轰轰烈烈,也许平平淡淡,但对走过蹉跎岁月的人来说,是一种历练,一种积累,一种抹不去,忘不掉的乡愁。.9.15日作者简介: 王顺利,曾在陕西省铜川市某央企从事工会职工文化宣传工作,曾在中,省,市,行业报刊发表各类体裁文学作品近百篇,多篇获不同奖项。近年重拾拙笔,在文学刊物和国内大型文学媒体平台发表近两百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杂文等。 《宁古塔作家》年度文学奖, 全国大奖赛征稿启事 为繁荣文学创作,培养更多的文学新人,讴歌新时代精神风貌,本次大赛主题不限,风格不限。参赛作品内容要求阳光向上,具有正能量,即日起面向全国征稿。 一、主办单位:宁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二、承办单位:宁安市作家协会、宁古塔作家网、宁古塔作家 1、组诗不超过5首,总行数不超过行;散文诗不超过字。每人限投一次。古体诗词,5首不超过行。散文、随感、小说七千字内。小小说1——3篇。 诵读参赛作品:音频1——3篇或首。 摄影作品5幅,手机拍摄或相机拍摄都可以。 本次参赛题目自拟。 2、文责自负。要求参赛稿件为未在纸质媒体上或网络平台发表的原创作品,非原创和抄袭稿件,一经发现或举报属实,取消其参赛资格。 3、此次来稿由《宁古塔作家》和《宁古塔作家网》编辑部负责收集整理,所有稿件需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单位、性别、年龄、地址、邮编、电话号码、
|
当前位置: 宁安市 >宁古塔作家年度文学奖王顺利家
时间:2021/9/29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宁古塔作家年度文学奖金美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