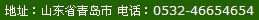|
怎样治白癜风 http://baidianfeng.39.net/a_kycg/160210/4769980.html引言基層社會的地域構造與聚落形態在先秦秦漢—魏晉六朝—隋唐長時段的發展演變,曾得到學者們的熱烈關注與討論[1]。目前較爲普遍的看法是,戰國秦漢以來,中央與基層的聚落形態就可以劃分爲有城郭圍繞的(城)邑,以及城邑之外散布的自然聚落;只是這些自然聚落具有多樣性,内部布局形態非一,而名稱各異,先秦時稱爲“落”“聚”“邑”“廬”等[2];考古發現漢代的自然聚落有遼陽三道壕、河南遂平小寨、河南内黄三楊莊等[3];六朝時的城郭外聚落有稱爲墟、野、場、林、丘、渚、溝、洲、浦等各種情况。侯旭東推測,大概晚至劉宋,“村”才從南方林林總總的自然聚落名稱中脱穎而出[4]。作爲律令制國家,唐建國伊始,就以《令》規範基層行政建置與聚落形態:“武德七年,始定律令:……百户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在邑居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村坊鄰里,遞相督察。”[5]以居住地爲原則,將自漢魏來或稱閭里,或稱里坊的城郭内封閉式地理單元固定爲坊;對城邑之外紛繁複雜的聚落進行整頓,在名稱上統一爲村,從制度上實施統一管理[6];同時在北朝、隋屢有變化的基層行政管理方式之外,重新採用鄉里鄰保的人口編組方法,這看似是向漢晉鄉里制的復歸,實則運轉着大一統帝國的生命活力。開元年間定令時,又對村、坊的設置情况進行了細化。“百户爲里,五里爲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内分爲坊,郊外爲村。”[7]開元二十五年()令:“諸户以百户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三)〔五〕家爲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别置村正一人。……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幹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8]第一,從制度層面將城郭、城外散聚之差别定格爲村坊之别,並强調此制普遍施行於兩京及外州縣;第二,明確基層行政單位和基層聚落的管理者以及他們在職掌上的差别;第三,規定里正/坊正、村正的任職、簡選標準。從《通典》所引唐令可知,里正和坊正是從同一群體内選拔並任用,也就是當處既設里正,掌户口賦役,又設坊正,掌治安,包偉民稱此爲唐代基層管理的“雙軌制”[9]。由此可理所當然的推出,鄉里制作爲人口編組與基層行政單位,應普遍適用於城内、郭外之聚落,即鄉里制與坊、村制並行。宫崎市定總結這種重疊現象爲“二重構造”説,可示意如下[10]:從律令的普適性來看,“二重構造”當行用於唐帝國全境,作爲首都的長安,當最爲示範。自唐以來即產生的以長安歷史文化、地理爲主題的城市文獻,細緻描述了城市内部的聚落形態、宫室宅邸、街道坊里[11];而其建築形制、外觀、規模、功用等,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開展的唐城考古工作中,又得到更加科學、數字化的表達[12]。借助西安出土唐人墓誌葬地的記載,外郭城以外,長安周邊的聚落形態也得到漸次呈現,具體成果見諸學者對長安、萬年兩縣下轄鄉、里、村及其位置的考證[13]。長安城門外,緊依外郭城牆即有村,村作爲自然聚落,與行政單位鄉、里並行。見於墓誌葬地有萬年/長安縣某鄉+某村,某里+某村,某鄉+某里+某村,某鄉+某村+某里等各種表達方式[14],村名有時在里名之下,這是村落住户稀疏,數個村湊足一里編組的情况;村名在里名之上,則是村落住户稠密,一個自然村下依户口劃分爲若干里的情况,直觀地表明了村與里的重疊。是否可以説,唐都長安城郭内外的聚落形態已全然明晰?恐怕不是。在長安城郭以内,里坊/坊里作爲被精心規劃的居住單元,幾乎佔據了研究者的全部視野。對於“百户爲里,五里爲鄉”的人口劃分是否亦行用於宫牆、坊牆、市牆、城牆林立的封閉區域這一基礎問題,卻很少見學者給出正面思考和系統論證。支持“二重構造”者,想當然以長安城内有鄉里,如宫崎市定、坂上康俊等。坂上氏以唐《令》規定里正與坊正從一個群體中選拔,具體職掌不同,由法條分析,長安城内肯定有鄉、里行政區劃[15]。但從事唐代長安歷史地理研究的學者無論從傳世文獻,還是出土墓誌中,基本没有檢索到位於外郭城之内的里名,尤其是鄉名[16],他們大部分選擇避開討論此問題,只是在估算長安及周邊人口數量時,直接以鄉作爲城外統計單元,以坊作爲城内統計單元,而不說明理由[17]。近來有學者正面論及這一問題,劉再聰以目前能掌握材料有限,不能得出唐兩京城内有鄉、里基層建制[18];成一農傾向於長安、洛陽城中的所有里之上都設鄉,但未做分析[19];坂上康俊的想法游移不定,支持“二重構造”説之外,又依據唐長安坊由數米高圍牆環繞的事實,認爲很難想像或一坊區劃數里,或若干坊組成一鄉、一里的情况在坊牆存在情况下如何運作;他嘗試提出了一種圓融的解釋,在兩京不存在人爲區分(鄉里)與自然區分(坊里)重疊結構的實質,是鄉里被坊制制約,而不能正確表現實態[20]。從以上研究回顧看,鄉里村坊制在唐長安的實施,看似明瞭,但鄉里制是否推行於城内,一直疑而未决。隨着近年來西安周邊唐人墓誌的新發現與刊布,我們又發現卒葬地記述中某鄉+某坊,某鄉+某里+某坊,某坊+某里,鄉名與坊、里名同見的情况[21],這是特例,還是以往不見的鄉里與坊制並行的明證?唐都長安的基層聚落形態究竟如何,與外州縣有何聯繫與區别?本文將嘗試對這一唐代區域地理研究中的難題予以解析與回應。一、唐長安城内的基層聚落形態要弄清鄉里制在長安城内的實施與否,需先對外郭城以内的聚落形態作考察。唐長安城承襲隋文帝開皇二年()六月至三年三月所築之大興城,“城東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東面通化、春明、延興三門,南面啓夏、明德、安化三門,西面延平、金光、開遠三門,北面光化一門。里一百六,市二。”[22]隋大興城沿用北魏洛陽城,北齊鄴南城的封閉式里制,在外郭之内規劃里,亦稱坊。坊之原意爲四周設有障壁的區域[23],北魏洛陽城之里(坊)規劃爲邊長三百步,周長一千二百步,一里見方(約合0.09k㎡)的封閉聚落,四邊環以坊牆[24]。隋大興城之坊亦有坊牆,文獻中可考索到一些在隋新都中築坊的信息,如《長安志》卷一〇記醴泉坊:“本名承明坊,開皇二年,繕築此坊,忽聞金石之聲,因掘得甘泉浪井七所,飲者疾愈,因以名坊。”[25]可知大興城建築的同時,城内的聚落——坊即被規劃,坊牆也被樹立。唐都在大興城基礎上擴建,永徽五年築京師羅郭[26],隋代的坊亦被沿襲,數量有調整。《唐六典》記開元時:“皇城之南,東西十坊,南北九坊;皇城之東、西各一十二坊,兩市居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27]以朱雀大街爲中軸線,街東南北向5行縱坊,東西向13排橫坊,共54坊、1市;街西南北向5行縱坊,東西向13排橫坊,共54坊、1市。規劃更爲精細。坊周圍有坊牆,據考古實測,牆基厚度約2.5-3m;坊按面積大小分爲三類:1.皇城以南、朱雀大街兩側四列坊,2.皇城以南其餘六列坊,3.宫城、皇城兩側的坊[28]。除第1類不開北門外,“每坊皆開四門,有十字街四出趣門。”[29]宿白先生指出坊内構造法:先用十字街將全坊分爲4區,每面各開一門,再用“井字巷”劃分,形成16區格局[30]。圖1唐長安城坊里分布圖圖2興化坊復原示意圖城内以筆直大道劃出一里見方的區域,築以坊,而坊内又4分、16分,在區劃上不斷地從大到小進行縮減,形成具有幾何精確度的基本單元;再與“人”結合,居以民衆,坊便成爲唐都長安最有活力的基層聚落,帶動着整座城市的運轉。唐都長安與漢長安、漢魏洛陽城相比,更加“平民化”,城市規劃中宫殿、官邸、宗廟、社稷等建築空間有所收縮,而民衆居住區擴大,坊囊括了不同社會階層的官民。 我們關心作爲長安基本居住單元或稱聚落的大小,就涉及到諸坊人口數量問題,據文獻記載,城東、中部,尤其是靠近東、西市諸坊人煙稠密,而南部諸坊,“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31]。史籍明確記載了興道坊的居民數,開元八年,興道坊因一夜暴雨陷爲池,“一坊五百餘家俱失”[32]。實際上,相關學者據文獻記載和考古實測的長安坊東西、南北步數估算,每坊的宅基面積約唐畝;而據唐均田制:“凡天下百姓給園宅地者,良口三人已下給一畝,三口加一畝;賤口五人給一畝,五口加一畝,其口分、永業不與焉。”[33]理論上一户可占一畝莊宅。如此,可推測長安城中坊的理想居住密度即興道坊的一坊户[34]。不過諸坊的居民密度差别較大,王社教先生曾詳細估算了城内坊各自的人口數,據其統計,住户達户的坊不下30個,其中義寧坊多達户,户數接近百户的僅靖善坊(大興善寺)、崇業坊(玄都觀)、大業、昌樂、安德、永達、道德、先行、延祚、平安、昌明等住户稀疏之坊[35]。要言之,長安城内的聚落坊,雖經過精確規劃,大小相倣,一里見方,但坊内人口數量時常多少不一。 同時,我們更應認識到坊這種聚落形態的封閉性,四周的坊牆和坊内區劃形成密閉空間,雖便於人口管理、治安維持,某種程度上也阻礙了人口的自由流動。長安城内實行宵禁,據唐《宫衛令》:“五更三籌,順天門擊鼓,聽人行。晝漏盡,順天門擊鼓四百搥訖,閉門。後更擊六百搥,坊門皆閉,禁人行。”[36]《新唐書》載:“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行嘂謼,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内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啓,鼓三千撾,辨色而止。”[37]城内坊統一由鼓聲爲准,由坊正負責坊門啓閉,早上五更二點自宫内曉鼓,諸街鼓順序敲動,坊門開啓,每晚鼓聲敲響關閉,不許出入;也就是説,日常生活中,各坊有一半的時間是作爲與外界隔絕的空間而存在。長安城内基層聚落的名稱,唐代文獻中主要稱爲坊,但亦有稱爲里的情况,而據西安出土唐人墓誌對誌主卒地(多在城内)的表述,西京長安/萬年縣某里第、某坊之里第、某坊里之私第[38],其中“里”與“坊”指代相同的地域空間,里爲坊之異稱,而不同於鄉里制中“百户”之里。這種情况,不獨出現在唐代都市。 二、唐長安城市坊里制的歷史淵源與現實運作1.“坊里”制與人口編制關係溯源唐都長安坊里制的性質必須放回到中國中古(漢唐間)都市發展的歷程中予以考量,已有許多學者做過類似工作。一般將唐制追溯至北魏平城——洛陽新型都市構造[39],不過宫崎市定已將唐代的坊制與漢代的里制相聯繫,以坊爲漢魏六朝里制之“復活”[40]。“坊里”制之“里”的原初含義,可追溯至漢代城邑中封閉的聚落閭里,《三輔黄圖》卷二記:“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有宣明、建陽、昌陰、尚冠、修城、黄棘、北煥、南平、大昌、戚里。”[41]之所以稱爲“里”,大概是在地域規劃上一里見方,一開始就僅指代一塊地域,如坂上康俊所言,具有屬地性[42]。東漢洛陽、曹魏鄴城中皆存在有意規劃的居民區——里,但具體型制不太清楚[43]。北魏舊京平城亦有人爲規劃的居住區坊,“其郭城繞宫城南,悉築爲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44]。由平城至洛陽,在鮮卑族漢化的願望驅動下,順應部族原有結構,以規劃齊整的“方三百步爲一里”的區塊安頓新型城民,促成了由上古而來的里坊制的嚴格化[45]。由於北魏洛陽令元軌之規劃,東魏北齊鄴南城之制“乃全襲北魏太和洛陽之舊規”[46],《隋書》記後齊鄴南城所屬鄴、臨漳、成安三縣,各下設“里”作爲基層單位,總計里(坊)[47]。北朝坊里制被隋、唐全盤接受,在這一長時段中,封閉區塊的名稱,早期正式名稱爲“里”,而俗稱爲“坊”;至隋文帝築大興城,建立起坊牆圍繞的嚴格坊里制,改以“坊”爲其正式稱呼,煬帝大業中又曾改“坊”爲“里”[48]。入唐,再度以律令規定正式名稱爲“坊”,而民間仍保留其舊稱“里”,對此宫崎市定、曾我部靜雄等已有梳理[49]。可見,稱“坊”爲“里”,並不是有唐一代的特殊現象。坊里制只是聚落劃分,其與歷代王朝人口編組的關係,學界亦有所論及,但主要强調其區别,如曾我部靜雄追溯了由《周禮》發展而來到唐都市里坊制的演變,敏鋭指出都市之“里”是以區劃爲稱,與百户爲里之鄉里制絕然不同,應完全區别開[50];邢義田先生認爲漢長沙國箭道封域圖中出現的“里”是因地形等自然條件形成的聚落,不是地方行政中的鄉里組織[51];張金龍以北魏洛陽城里坊制下之“里”以面積大小爲准,與三長制下以民户數量爲准的“里”有本質區别[52];張劍指出北魏洛陽有城内坊里、城外鄉里之分[53],等等。卻較少考慮二者之間的聯繫,或者説二者是否重疊。我們對兩漢長安、洛陽,曹魏鄴城中的閭里(坊里)的内部構造並不清楚,這裏從具有成熟里坊結構的北魏洛陽談起。齊東方曾推測北朝都城人口編組應以“三長制”爲基礎[54];張金龍、張劍則利用《洛陽伽藍記》等傳世文獻及北朝墓誌,對洛陽城及其周邊的地理進行了全面研究,發現北魏洛陽城所在的洛陽縣域内僅設1鄉——都鄉,下轄12里,另直轄41里,而墓誌中出現的其餘鄉里連稱地名,應屬洛陽城外[55];也就是説,在洛陽内城和外郭城中的里坊,大部分直屬於縣,而未被納入鄉里人口編制中[56]。張金龍還指出,北魏全國通行的“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57]的地方基層行政制度“三長制”也没有在首都洛陽出現[58]。由於東魏北齊鄴南城毀於戰亂,其型制較爲難考,王仲犖、牛潤珍等學者借助北朝墓誌,先後添補了鄴城下轄之里名、坊名[59],墓誌誌主卒地多寫作鄴縣/都/城某某里/坊之舍/宅/第,而葬地則表述爲某某鄉某某里,可推測鄴都郊外實行了鄉里制,但城内依然只有規劃的坊里,坊上不設鄉。從北齊令,我們也可較爲清楚獲知當時坊里制與人口編制的關係:“人居十家爲鄰比,五十家爲閭,百家爲族黨。一黨之内則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有十四人,共領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户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60]北齊的編户制度與三長制略有不同,有鄰比、閭、族黨等單位;但城邑之内,分爲坊里,無論一坊户口多寡,僅以聚落爲單位,置里正、里吏,隅老,而並不按人口數量設置黨族、閭正、鄰長等,也就是説,鄴城内坊里亦不納入基層人口編組。開皇九年二月,“制:五百家爲鄉,正一人,百家爲里,長一人”[61],表明基層人口、行政編制向漢晉鄉里制復歸,大興城内的坊是否納入鄉里人口編制?史籍無正面記載,但從西安出土隋代的兩方墓誌中我們發現了一種比較獨特的地域表述法,《趙長述誌》記:“開皇十七年四月十九日雍州長安縣修仁鄉故民趙長述銘,住在懷遠坊。”[62]《楊士貴誌》記:“仁壽元年正月廿六日長安縣禮成鄉洽恩里住居德坊民故楊士貴銘記。”[63]懷遠坊在隋大興城街西自東向西第四排,北臨利人市,近西側城牆;居德坊在懷遠坊更西一排,緊鄰金光門;修仁鄉、禮成鄉,據學界對隋大興城周邊地名的考訂,皆在外郭以外,出金光門,相當於今西安西郊杈楊村一帶[64]。趙、楊二人居住在城内坊里,在户籍編制上卻編入城外鄉里,説明城内不存在鄉里户口編制。綜上,自北朝至隋,城郭内似皆不存在作爲聚落形態的坊里與作爲人口編組的鄉里重疊並存的情况。2.坊里制在唐都長安的運作唐代城郭外的自然聚落村是被納入鄉里人口編組的,本文第一節提到存在小於里的村,若干村爲一里;大於里的村,若干里爲一村的情况,齊東方據此推測唐代城市中里與坊應有類似關係[65]。上文又介紹了唐都長安諸坊的人口密度,極不均匀,有的坊内户口規模在百户左右,或相當於百户之里,而有的坊轄五百户,相當於一鄉,另有不少坊容納千户以上,是否坊下劃數個里?楊寛就曾據《李娃傳》《太平廣記》故事中長安城内“里胥”、“里長”的記載,推定城内諸坊下有十多個到幾十個里正[66],實際情况是否如此?試想,城内的坊里,即每個獨立空間内的户口數不可能正好是户、户,也就是説,若進行百户爲里,五里爲鄉的人口編組,就必然存在着若干坊共同編爲一鄉,或者較大的坊編爲若干鄉、若干里後,剩餘的片區需與臨近坊再編組成里、鄉的情况。問題在於,長安城内的基層聚落是一種封閉性的地域單元,各單元之間有坊牆阻隔,若不同坊之地劃歸同一鄉、里,難以想像鄉里定期跨越坊牆進行“按比户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67]等事务;况且各坊之門僅在白天開放,夜間緊閉。從現實運作的角度看,人口高度聚集的城市必須建立一種基於地域的管理制度。我們再次回看北魏以來的都市管理,《洛陽伽藍記》卷五記北魏洛陽城:“方三百步爲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68]張金龍的理解是,里中以門爲單位設置管理人員,四門共置里正8人,吏16人,門士32人,計56人[69]。當從其説。東魏武定年間元孝友奏,言及鄴都,“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况外州乎?”[70]北齊令:“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户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71]説明鄴都内的置吏,是以聚落爲單位,所置里正、里吏是聚落管理者,有定員,其員額並不隨聚落内人口多少而發生變化。入隋,大興城内里坊亦只是“每里置里司一人”[72]。如此推想,唐長安城内諸坊/里,亦應僅有基於區域的管理者,所不同的是,由於“坊”成爲城市内封閉聚落的法定名稱,其管理者隨之稱爲坊正[73]。都城内的坊里往往爲人口薈萃地,構成規模龐大的地域單元。這種大單元僅置數名管理者,可否承擔人口管理、賦役征派,坊門啓閉、坊内治安等多重事務?宣武帝末年河南尹甄琛上表討論京邑的管理問題,提到在里正上置經途尉與六部尉,“司察盜賊”[74],説明由於聚落管理者負擔較重,一些職掌由他官分有。而據唐令記載,首都及其他城市的坊正,僅“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則是否與北魏相類似,城内存在其他管理人員以相分工?張國剛先生在觀察唐代基層管理者時曾敏鋭地感覺到,雖然存在里正掌行政,村、坊掌治安的分工,至唐中後期,由於代表實際居住地,村、坊日益成爲國家政策關注重點,唐代基層管理愈益按自然村模式進行;玄宗之後,村正甚至直接面臨催征賦役的任務[75]。這種現象可能並不僅僅在中唐以後出現在城郭以外的自然聚落,在國家規劃建成的首都長安,應亦存在人爲劃分的居住聚落坊與基層行政區劃的重疊;聚落的管理者坊正,同時承當行政職責,不再另設鄉官里吏。楊寛徵引唐人小説中的里胥、里長,應只是坊正之别稱,而非行政單位“里”之長官。曾我部靜雄提示,日本藤原、平城、長岡、平安諸京皆實行一元化的條坊制,而里僅存在於城外,因此京内基層管理者坊令/坊長民治、治安兩者並掌[76],見《養老令·户令》之“置坊長條”:“凡京,每坊置長一人,四坊置令一人。掌檢校户口,督察奸非,催驅賦徭。”[77]一般的觀點以爲,日、中中古都市管理方式有别,中國爲里正、坊正雙軌制[78],但據以上分析,至少就長安而言,可能也是單軌制。這一判斷可以得到印證。北宋《兩朝國史志》記太祖、太宗:“諸鄉置里正主賦役,州縣郭内舊置坊正,主科税。開寶七年,廢鄉,分爲管,置户長,主納賦,耆長主盜賊、詞訟。”[79]北宋立國之初的所謂“舊”,顯然是指唐五代,也就是説,不僅是在宋代坊正承擔各種行政管理職能,唐五代城郭内的坊正亦“主科税”,負責推排户籍,差發夫役,察奸彌盜,承受公事等事務。坊正由社區治安管理者而成爲全面的基層管理者,在基層日常政務運作中的根本依託是鄰保、伍保制,唐令所謂“四家爲鄰,五家爲保”[80]。鄰保制廣泛實行於城鄉,作爲最爲基礎的人口組織單位,一方面在治安上爲村坊服務,如元和十二年()“敕京城居人五家相保,以搜奸慝”[81];一方面在賦役攤派上爲鄉里服務。這種基層組織,將行政與治安統合而掌之。此外,據包偉民研究,宋代城市中的賦税、差役都以坊(實際居地)爲元單位徵發[82]。《宋史·食貨志》記:“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城郭之賦,宅税、地税之類是也。”[83]“城郭之賦”多以居民在城郭内擁有園宅爲基礎徵發,而夫役則按坊“排門差撥”。唐代城市居民的户口編制、賦役征派情况不明,不過牛來穎先生也據《延喜式》推測,唐都長安或許存在工商業者交納“地子”用於都市公共建設的情况[84]。基於聚落而置的坊正,完全有條件處理基於居住地而開展的各項行政事務。三、唐都長安“無鄉里”説與“二重構造”討論長安城市基層建制,最可依憑的資料是唐人自己的地域描述,上文已據西安出土唐人墓誌中的卒地記載討論城内地域單位,里與坊異名而同指,僅指代聚落名稱,而不存在統轄百户行政之里。而對於出現在誌主葬地中的長安/萬年縣某某鄉某某里,學者曾利用墓誌出土時地信息,將其一一對應到唐代長安地圖中,發現這些鄉里都分布在兩縣在外郭城以外的區域[85];傳世文獻所記唐鄉名,也都在長安周邊,不在城内。種種跡象提示我們,或許唐都長安無鄉里。上述推測最大的未安之處在於,《唐令》曾明確提及,“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幹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86]且作了里正掌賦役、坊正掌治安的分工,也就是説,里正、坊正在國家法令的語境中是同時存在的,鄉里制與坊制應在唐帝國轄境内重疊,這就是上言宫崎市定所提“二重構造”[87]。如果作爲首都的長安都不存在二重構造,何以解釋律令的效力? 要疏通這一矛盾,要先把目光轉移至唐代地域廣大的地方城市。在地方城市,確實存在坊上設鄉、坊下轄里的情况,坊制與鄉里制並行,如魯西奇對唐代漢水流域州縣城市的個案研究[88]。問題又來了,上文依據長安坊里制的封閉性提出鄉里户口編組方式無法跨越坊牆而存在,地方城市中亦實行坊里制,卻能融入鄉與里?要解釋這第二個問題,我們要關注考古、歷史地理學者對唐代地方城市型制、規模、實質形態的研究。宿白先生較早關注隋唐城址,將其分爲京城、都城、大型州府城、中、小型州府城、縣城幾個等級,其中小型州城、縣城僅轄1坊[89];可以推想,大部分的縣級城市,城内居民數量有限,或不足一鄉規模,坊上設鄉,當是普遍情况。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學者們在探討地方城市型制時普遍認識到,制度規定之下,城牆、坊牆在地方城市中是否普遍修建,很難有確切結論[90]。愛宕元對唐代州縣級城郭的系統研究顯示,可考築城年代的個城郭,有90個是唐天寶後修築的(占55%)[91];魯西奇對唐前中期漢水流域58座州縣治所城市逐一排查,指出只有2座城郭爲隋及唐初新築或重修,有40座沿用魏晉南北朝時舊城垣,其餘16座在唐前期可能並無城郭,進而有大多數州縣治所在唐前中期(天寶以前)並未修築城垣的推斷。城牆的建築情况尚且如此,恐怕更談不上仿照兩京制度規劃城内坊里了。魯西奇又指出,唐代地方城市中雖有里坊名目,但未見里坊爲封閉式記載,或者没有坊牆,所謂唐中葉以後坊牆的倒塌,“中世紀城市革命”,或許只是某種理論預設下對史料的“選精”“集粹”[92]。聯想到唐令中“二重構造”法,應正是唐前期城坊制度未定型情况下地方城市的寫照。由於當時城市之城郭主要延續南北朝之戍城,規模小,主要部署官署、軍營等軍政設施(稱爲子城),故而城内不能容納太多居民,普通民衆大多選擇附郭居住,或被包入大城(羅城),或没有;其居住形態,據魯西奇對漢水流域城市的研究,多是以街巷爲中心,向兩邊展開的街區,這些街區下亦劃爲坊,但往往不築坊牆,爲開放的山水田園區。以唐襄陽府治所襄州城爲例:圖3唐代襄州城内外里坊示意圖據魯西奇《城牆内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的形態與空間結構》頁示意圖改繪。子城内填塞山南東道節度使、襄陽縣衙署,空間狹促,魯西奇據墓誌考證出靖安、旌孝、明義三里(坊)名,這三個里坊或有封閉性。但子城外西、南、東三面有廣大居住街區,這些街區下亦有坊,如城南安遠坊、南津坊,這些坊只是居住區塊名稱,没有封閉性,在行政管理中,亦編入鄉;據墓誌記載,城南兩坊屬鳳林鄉;而城東有崇教里(坊),屬殖業鄉,城西春台鄉下有漢陰里、檀溪里(坊)[93],這些里名皆出現在誌主卒地(某某里之私第),應爲坊里之“坊”,因而存在鄉里制與坊制的重疊。這或許能代表唐南方城市的一般情况。包偉民在研究宋代地方財政史過程中曾提出制度在執行過程中的“地方化”“非制度化”現象[94],我們嘗試以之解釋鄉里村坊制在唐長安的施行問題。長安作爲唐帝國首都,一代制度、文物皆是獨一無二的,由於城市建設、管理的特殊需要,以坊里形成綜合性管理單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唐令所敘述的,是唐代地方城市的一般情况。但唐令並非完全没有照顧到長安和洛陽的特殊性,《賦役令》唐15條是對唐前期諸色人的規定:諸正、義及常平倉督,縣博士,州縣助教,……諸州醫博士、助教,兩京坊正,縣録事,里正,州縣佐、史、倉史、市史……並免課役……。[95]諸色人中的一些人群,屬於唐代地方行政系統中的“雜任”[96],因固定在官府服役而免課役。令文在列舉州縣雜任時,單單拈出兩京坊正與里正對舉。渡辺信一郎、牛來穎、趙璐璐等認爲是因爲唐前期坊制先從兩京實行,在地方尚不普遍[97]。但依據上文介紹,唐代外州縣城都有坊之設置(或許不存在坊牆),爲何要在坊正前貫以兩京之限定?本文以爲,正是由於兩京城郭内没有里正之設,僅有坊正,而坊正應全面承擔本區域内的行政、治安、民事等等各項事務。國家在定令時,對兩京的這種特例有所考慮。四、規劃與順應:對城中鄉的一種解釋唐都長安“無鄉里”説是得到大量出土文獻支持的,但來自墓誌還有一些長安某鄉某里某坊的記載,似表明城中有鄉有里,從事長安城郊鄉里村考證的學者遇到類似情况,多簡單解釋爲雖然制度規定上在城曰坊,在鄉曰里,但每混稱[98]。雖然數量極少,但我們無法漠視這些特例的存在。在坂上康俊之後,筆者嘗試盡可能全面收集了隋唐長安城中鄉與城外坊的例證,依時間順序列舉如下,於每例後,先依常理稍加分析:例1,《梁龕誌》記:“大隋開皇十四年歲次甲寅四月乙丑十五日乙卯,大興縣安道鄉常樂坊民梁龕銘記。”[99]隋初平民墓誌較簡單,此處地理記述的是梁氏户籍地,還是居地,不太清楚,常樂坊在隋大興城最東一排自北向南第六坊,東鄰春明門[];安道鄉,未見諸傳世文獻及墓誌記載,應屬大興縣下之鄉。此例確實表明,隋都城内之坊上設鄉。例2,《安萬通磚誌銘》銘文末作:“永徽五年()十二月一日,長安縣安國鄉普寧坊。”[]該誌出土於西安市西郊棗園村西,棗園村以東爲龍首鄉,西爲安國鄉,屬長安縣;普寧坊爲長安城西北角落一坊,緊臨開遠門。李健超、杜文玉等都以普寧坊、安國鄉分别爲安萬通的卒(居住地)、葬地[],但誌文中提及安氏“永徽五年十二月一日,葬於城西龍首原”,可知文末同日期下之“安國鄉”“普寧坊”應爲一處地名,即誌主葬地。隋、唐《喪葬令》皆有去京城七里之内不得埋葬的規定[],長安城内的坊名不可能出現在墓誌葬地書寫中,安國鄉普寧坊應在城外,或許此處之普寧坊實爲安國鄉下“普寧里”之誤記?我們又注意到敦煌P.《十戒經盟文》的信息:大唐景雲二年,……清信弟子王景仙……詣雍州長安縣懷陰鄉東明觀里中三洞法師中嶽先生張〔泰〕,受十戒十四持身之品,修行供養,永爲身寶。[]東明觀,在普寧坊東南隅,三洞法師居於“雍州長安縣懷陰鄉東明觀里中”,正説明城中坊確實與鄉里編制重疊,聯繫《安誌》,恐亦非誤記。圖4《安萬通磚誌銘》中的鄉、坊位置示意圖例3,《唐董君夫人戴滿墓誌》:“夫人諱滿,……粵以顯慶四年()歲次己未二月戊申朔廿五日壬申卒於長安縣弘安鄉嘉會坊私第。”[]弘安鄉,從現有墓誌及傳世史料未見長安、萬年縣下有此鄉名;嘉會坊在街西第四街自南向北第五坊,西接待賢坊,靠近延平門,屬城郭邊緣之坊。此例爲誌主卒地,應確在長安城内,但坊上有鄉。例4,《張府君妻田雁門縣君墓誌》記志主:“以其年(天授二年/)六月三日,遷窆於城東龍首原長樂鄉王柴村南一里,向南與壽春坊路通也。其地北帶涇渭,南望秦原,四塞之固,名箸安葬,自無殃柩,必出公侯。”[]萬年縣長樂鄉有王柴村[],但所謂“村南一里,向南與壽春坊路通也”,令人殊爲不解,唐代長安城有城牆,坊有坊牆,皆爲封閉式,進出需通過坊門與城門,長樂鄉在通化門外,其下之村怎能有路與城内之坊相通?且查壽春不見於長安坊名,依據上述唐都長安的埋葬制度,長安城内的坊不可能是葬地。以上都説明壽春坊應爲誤記,長樂鄉下有壽春里,“坊”應爲“里”之訛誤。例5,《折夫人曹氏墓誌》記其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廿三日遷窆於金光坊龍首原之禮也”[]。依唐《喪葬令》規定,此處金光坊亦不可能是城内之坊,查長安縣龍首鄉有金光里,因在金光門外而得名,此處坊或爲“里”之訛誤。例6,《崔蕃墓誌》記其大和七年()“十一月八日歸葬於京兆□□縣寧安鄉曲□域”,《墓誌彙編》録文如此[],坂上康俊以爲當録作“京兆府萬年縣寧安鄉曲江坊”[],細審圖版,“江”字没有問題,但其下一字僅存左半邊之“土”,無法辨識[]。《楊崇夫人甘氏墓誌》記其乾符三年()葬京兆府萬年縣寧安鄉曲池坊[]。寧安鄉屬萬年縣,緊鄰長安東南角,而曲池坊爲長安城最東南角一坊,兩者相毗鄰,但兩例皆誌主葬地,應在城外,注意到寧安鄉下恰有曲池里和曲江池村,則《甘氏墓誌》中之“曲池坊”應爲“曲池里”之訛誤,而《崔氏墓誌》本當作“曲江域”,坂上康俊之改録不可從。 例7,《續高僧傳》卷二七《釋玄覽傳》:“京東渭陰洪陂坊側。”[]此處“渭陰”當爲鄉名,其地在禁苑以北,緊靠渭河,爲萬年縣較北之鄉,《西安歷史地圖集》以其下有洪陂里[],論者皆以此處“坊”爲誤記。例8,《太平廣記》卷三六一《牛成》:“京城東南五十里,曰孝義坊。”[]查長安城内無坊名孝義,但此坊在京城東南五十里,考其里數,唐萬年縣境東西37里,南北27里,據《長安志》載,較遠之白鹿鄉在萬年縣南四十五里,東接藍田縣[],則孝義坊極有可能屬藍田縣。考諸以上特例,除明顯訛誤或其它理由外,尚不能排除鄉坊連稱的有效特例是例1、2、3,這三例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從屬於鄉的坊,常樂、普寧、嘉會坊都處於城郭邊緣,而坊所屬之鄉,如安國鄉,在長安城西北,臨龍首鄉,距城不遠;甚至已被排除的例6,曲池坊亦在城内邊緣,而寧安鄉在城外緊靠外郭城,坊與鄉毗鄰,本可相連而爲一體。坂上康俊研究長安周邊地理時注意到,長安城内的坊名與城外鄉名有重復的情况,如長樂鄉、長樂坊,永平鄉、永平坊,布政鄉、布政坊,很難説它們之間全無關係,以這種情况可解釋爲包含此坊的鄉延伸至城外[]。問題在於,都城内的坊爲獨立基層單元,外隔坊牆,與城外又隔城牆,爲何會出現跨越高牆,連接城郭内外的鄉?我們須將這個疑問置於北朝至隋唐長安地區歷史地理變遷的向度上來考量。魏周長安城沿襲漢長安城舊址,而隋文帝開皇中,於漢長安城故址東南另覓新址置大興城,新王朝營建新都的舉措,造成了長安及周邊區域聚落形態的巨大變化,原北周的城郭被劃入禁苑或演變爲鄉村,而北周時爲鄉村的大片區域被劃爲宫禁或獨具匠心地設計爲具有幾何學精確度和對稱性的整齊劃一的封閉式里坊。圖5秦、漢至隋關中都城位置遷移示意 據妹尾達彥《隋唐長安城と郊外の誕生》,《東アジア都城の比較研究》,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年,頁。這種地理變遷,在文獻中可尋找到一些蹤跡:《舊唐書·五行志》:“隋文時,自長安故城東南移於唐興村置新都,今西内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今有大槐樹,柯枝森鬱,即村門樹也。有司以行列不正,將去之,文帝曰:高祖嘗坐此樹下,不可去也。”[]《太平廣記》:“長安朝堂,即舊楊興村,村門大樹今見在。初周代有異僧,號爲棖公,言詞恍惚,後多有驗。時村人於此樹下集言議,棖公忽來逐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遷都意。”[]北朝之唐興村、楊興村,入隋被括入宫城,地當宫城南承天門,以及(太極宫)朝堂。又《歷代名畫記》卷三記隋興化坊空觀寺:“本周時村佛堂,遶壁當時名手畫,佛堂在寺東廊南院,佛殿南面東西門上,袁子昂畫,又有三絕。”[]《寺塔記》記長樂坊安國寺:“佛殿,開元初,玄宗拆寢室施之。當陽彌勒像,法空自光明寺移來。未建都時,此像在村蘭若中,往往放光,因號光明寺。寺在懷遠坊,後爲延火所燒,唯像獨存。”[]隋唐都城内的坊里空間,在北周時皆爲城郭之外的散村。《兩京新記》殘卷更記載了隋初在北朝郊野區域築坊的情形:“金城坊。本漢博望苑之地。初移都,百姓分地板築,土中見金聚,欲取便没。”[]試想,北朝郊野的村聚中實行鄉里人口編制,而當新都的城牆、坊牆在這些區域中被樹立時,舊鄉里的轄區,可能被全部包裹入新城,代之以新式坊里,也有可能部分括入新城,跨越了人爲築造的村坊分界。在相當一段時間内,尤其是坊牆、外郭城牆未能普遍修繕完備的情况下,對於舊鄉里,極有可能順應其原有轄區,從而造成已劃爲城内坊的部分,仍從屬於緊鄰城郭的鄉里,故而出現城中鄉這種少見的現象。考察上述有效特例的時間,例1在隋代大興城初建工程完成後不久,例2、3皆在唐高宗統治期。隋大興、唐長安城的修築,都不是一蹴而就,而經歷了相當長的修補、增築過程。隋文帝開皇二年—三年初城大興,至煬帝大業九年()“三月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有增築;大業末楊玄感反,又增築之[]。入唐,又對大興城進行擴建,永徽五年十一月:“築京師羅郭,和雇京兆百姓四萬一千人,板築三十日而罷,九門各施觀。”[]考古工作者認爲,這次主要是重修門道的木構、城門樓觀,將路面加高,夯平[]。又,“開元十八年()四月一日,築京城,九十日畢”[]。二十二年,户部尚書、京師留守杜暹還曾“抽當番衛士,繕修三宫,增峻城隍”[]。城牆在開元年間又經過整修。可能到這時,長安城的外郭城、城門、城内諸坊的坊牆才被大規模地樹立起來而成爲定制。注意到例2,安萬通埋葬時間正好是永徽五年,當時長安城西北角的外郭很可能正在修建中,位於安國、懷陰兩鄉交叉點的這塊地域,被括入城内,甫成就新的“普寧坊”,墓誌書手在葬地記述中,依然延續舊地名,將“普寧坊”置於安國鄉下,造成了城内“坊”從屬於城外“鄉”的特例。這種包夾城郭内外區域的鄉,在隋、唐前期曾存在過,但在城坊普遍建立後的首都,或已無法作爲基層行政單位而管理、運作。《天寶十道録》殘卷記唐前期長安縣轄79鄉,萬年縣下轄62鄉[],而到《太平寰宇記》、《長安志》反映的唐中後期長安縣、萬年縣下轄鄉數目分别減至59、45鄉[],由此看來,唐中期以後,長安及周邊的鄉里區劃確實進行過調整。通過以上的梳理,可對本文的論點作總結如下:1.唐代長安都城建制、管理制度遠紹秦漢,近承北魏,從北魏洛陽城開始的歷代都城,外郭城内都只存在里坊一元構造,而並不再進行另外的户口編組。2.唐長安城内的坊已由單純的聚落、社區,演變爲兼具治民、治安等多重職能的基層統治單位,坊正之外,並無其他鄉里管理人員的設置;也就是説,無論從歷史傳統,還是現實運作的角度,鄉里制皆無在都城推行的必要。3.唐都長安無鄉里的情況,是唐代基層建制在超大都市的變通,得到大量傳世與出土文獻的印證,西安出土唐人墓誌中零星出現的城中鄉與城外坊,或是記載有誤,或是隋至唐初都城初建過程中在城鄉交界處的特殊情況。編者按:本文原載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2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年,第—頁。[1]魯西奇總結日本學者的中國古代鄉村研究存在兩種理路,一是從“都市國家”理論預設出發,考察先秦至南北朝是否存在着“城居”向“散村”之演化,二是從“村落共同體”理論預設出發,考察傳統中國鄉村是否存在相對自治的“共同體”。詳所撰《古代鄉村聚落形態研究的理路與方法》,《歷史學評論》第1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年,—頁。[2]参考池田雄一《中国古代における聚落の展开》、《中国古代の聚落形态》,氏著《中国古代の聚落と地方行政》,汲古書院,2年,39—47、65—88頁。[3]東北博物館《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考古學報》年第1期,—頁;河南文物研究所《河南遂平縣小寨漢代村落遺址水井群》,《考古與文物》年第5期,41—45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縣文物保護管理所《河南内黄縣三楊莊漢代庭院遺址》,《考古》4年7期,34—37頁;邢義田《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黄寛重主編《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册》,聯經出版公司,9年,17—48頁。[4]侯旭東《漢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論“邨”“村”關係與“村”的通稱化》,《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册》,—頁。[5]《舊唐書》卷四八《食貨上》,中華書局,年,頁。[6]劉再聰《唐朝“村”制度研究》,厦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3年,30—37頁。[7]《唐六典》卷三《尚書户部》,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年,73—74頁。[8]《通典》卷三《食貨三》,中華書局,年,63—64頁。[9]觀點見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中華書局,年,頁。[10]宫崎市定《中國における村制の成立——古代帝國崩壞の一面》,《東洋史研究》18卷4號,年;漢譯本《中國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國崩壞的一面》,《宫崎市定論文選集》上卷,商務印書館,年,39—40頁。[11]如《兩京新記》、《歷代名畫記》、《寺塔記》等,辛德勇稱之爲“城市文獻”,妹尾達彥稱之爲“都市志”,參考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緒説,三秦出版社,年,1—8頁;妹尾達彥《韋述〈兩京新記〉與八世紀前葉的長安》,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3年,12—13頁。。[12]參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考古學報》年第3期,79—94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年第11期,—頁。[13]相關研究成果頗豐,如武伯綸《唐萬年、長安縣鄉里考》,《考古學報》年第2期,87—99頁;《唐代長安郊區的研究》,《文史》第3輯,年,—頁,氏著《古城集》,三秦出版社,年,88—頁。愛宕元《唐代兩京鄉?里?村考》,《中國聚落史の研究》,刀水書房,年,58—68頁;《唐代兩京鄉里村考》,《東洋史研究》40卷3號,年,收入氏著《唐代地域社會史研究》,同朋舍,年,3—23頁。杜文玉《唐長安縣、萬年縣鄉里補考》,史念海主編《漢唐長安與關中平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年增刊,—頁。史念海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唐長安縣、萬年縣鄉里分布圖”,西安地圖出版社,年,78頁。等等。[14]如上幾種表述方式,均見於愛宕元所條列的萬年、長安縣所管鄉里村名,氏著《唐代地域社會史研究》,3—23頁。[15]參坂上康俊《唐代の都市における鄉里と坊の關係について》,《東北亞歷史財団企畫研究》51《8世紀東アジアの歴史像》,年,—页;漢譯本《論唐代城市鄉里與坊的關係》,周東平、朱騰主編《法律史譯評》,北京大學出版社,年,89—頁。[16]做長安、萬年縣鄉里村名考證的學者如武伯綸、愛宕元、杜文玉、尚民傑等,基本都認爲唐代的基層行政單位是城内分爲坊,郊區分爲鄉與里。[17]觀點見李之勤《西安古代户口數目評議》,《西北大學學報》年第2期,45—51頁;愛宕元《唐代京兆府の户口推移》,唐代史研究會編《律令制——中國·朝鮮の法と國家》,年,收入氏著《唐代地域社會史研究》,95—頁;龔勝生《唐長安城薪炭供銷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年第3期,—頁;妹尾達彥《唐長安人口論》,《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中国古代の國家と民衆》,汲古書院,年,—頁。[18]劉再聰《唐朝“村”制度研究》,42—43頁。[19]成一農《里坊制及相關問題研究》,《中國史研究》年第3期,頁。[20]坂上康俊《論唐代城市鄉里與坊的關係》,頁。[21]這樣的特例更多見於洛陽出土墓誌,坂上康俊也收集到一些,《論唐代城市鄉里與坊的關係》,—頁。但洛陽的情况,暫不在本文考察範圍内。[22]《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中華書局,年,頁。[23]關於作爲首都城内區塊“坊”的原始含義,曾我部靜雄做了梳理,見《都市里坊制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58編第6號,年,—頁。[24]《洛陽伽藍記》卷五記北魏:“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萬九千餘。廟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里,里開四門。”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中華書局,年,頁。《魏書》卷一八記廣陽王元嘉“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週一千二百步”,頁。[25]宋敏求《長安志》,辛德勇、郎潔點校,三秦出版社,年,頁。[26]《舊唐書》卷四《高宗上》,73頁。[27]《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頁。[28]長安城内坊里設計及其形制規模,參考宿白《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年第6期,—頁;妹尾達彥《韋述的兩京新記與八世紀前葉的長安》,《唐研究》第9卷,9—52頁。[29]《長安志》卷七,頁。[30]宿白《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頁。[31]《長安志》卷七,頁。[32]《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頁。[33]《唐六典》卷三《尚書户部》,75頁。[34]賀從容從建築學角度對長安城内的宅基面積進行了推算,詳所撰《隋唐長安城坊内百姓宅地規模分析》,王貴祥主編《中國建築史論彙刊》第3輯,清華大學出版社,年,—頁。[35]王社教《論唐都長安的人口數量》,《漢唐長安與關中平原》,年,88—頁。[36]《唐律疏議·雜律》“犯夜”條疏議引,中華書局點校本,年,—頁。[37]《新唐書》卷四九上《百官志》,中華書局,年,6頁。[38]坂上康俊氏利用出土墓誌,對卒於長安、洛陽城内之人的歿故地表述方式有系統總結,可參所著《論唐代城市鄉里與坊的關係》,—頁。[39]學者在討論隋唐都市坊市制度時,多稱其源於魏晉,參齊東方《魏晉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學的印證》,《唐研究》第9卷,60、64頁;張金龍《北魏洛陽里坊制度探微》,《歷史研究》年第6期,51—67頁;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頁。[40]宫崎市定《漢代の里制と唐代の坊制》,《東洋史研究》第21卷第3號,年,27—50頁。[41]《三輔黄圖校注》,何清谷校注,三秦出版社,6年,頁。[42]坂上康俊《論唐代城市鄉里與坊的關係》,98—頁,[4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鄴城考古工作隊《河北臨漳鄴北城遺址勘探發掘簡報》,《考古》年第7期,—頁。[44]《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列傳》,中華書局,年,頁。[45]齊東方《魏晉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學的印證》,60—65頁。[46]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之《禮儀附都城建築》,三聯書店,9年,80頁。[47]見《隋書》卷二七“後齊”:“鄴、臨漳、成安三縣令……鄴又領右部、南部、西部三尉……凡一百三十五里,里置正。臨漳又領左部、東部二尉……凡一百一十四里,里置正。成安又領後部、北部二尉……七十四里,里置正。”,中華書局,年,頁。[48]《隋書》卷二八《百官志》:“京都諸坊改爲里,皆省除里司,官以主其事。”(頁)[49]參宫崎市定《漢代の里制と唐代の坊制》,27—50頁;曾我部靜雄《都市里坊制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頁。感謝石洋兄惠寄日文資料。[50]曾我部靜雄《都市里坊制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頁。[51]邢義田《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27—34頁。[52]張金龍《北魏洛陽里坊制度探微》,《歷史研究》年第6期,65—67頁。[53]張劍《關於北魏洛陽城里坊的幾個問題》,洛陽市文物局、洛陽白馬寺漢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編《漢魏洛陽故城研究》,科學出版社,0年,—頁;《洛陽出土墓誌與洛陽古代行政區劃之關係》,趙振華主編《洛陽出土墓誌研究文集》,朝華出版社,2年,—頁。[54]齊東方《魏晉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學的印證》,56—57頁。[55]張劍《關於北魏洛陽城里坊的幾個問題》,—頁;張金龍《北魏洛陽里坊制度探微》,64—67頁。[56]都鄉情况除外,北魏洛陽城内洛陽縣下僅此一鄉,應是對漢晉以來縣級治所稱都鄉舊制的模仿。可參看寇克紅《“都鄉”考略——以河西郡縣爲例》,《敦煌研究》年第4期,85—94頁。[57]《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頁。[58]張金龍《北魏洛陽里坊制度探微》,51—67頁。[59]王仲犖《北周地理志》卷一〇,中華書局,年,—頁。牛潤珍《東魏北齊鄴京里坊制度考》,《晉陽學刊》9年第6期,81—85頁。[60]《通典》卷三《食貨三·鄉党》,62頁。[61]《隋書》卷二《高祖纪》,32頁。[62]王其禕、周曉薇主編《隋代墓誌銘匯考》,號,線裝書局,7年,—頁。[63]《隋代墓誌銘匯考》,號,頁。[64]參考王靈《隋代兩京城坊及其四郊地名考補——以隋代墓誌銘爲基本素材》,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7年。[65]齊東方《魏晉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學的印證》,57頁。[66]楊寛《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3年,—頁。[67]《通典》卷三《食貨三·鄉黨》,63頁。[68]《洛陽伽藍記校釋》,—頁。[69]張金龍《北魏洛陽里坊制度探微》,《歷史研究》年第6期,61頁。[70]《魏書》卷一八《太武五王列傳》,頁。[71]《通典》卷三《食貨三·鄉黨》,62頁。[72]宋敏求《長安志》卷七,頁。[73]成一農認爲北朝至隋,城中可能没有管理坊的胥吏,坊正之置較晚,甚至遲至唐代,參《里坊制及相關問題研究》,—頁。無論坊正一職何時出現,北朝隋唐大都市基於地域的管理制度一以貫之,只是管理者的名稱前期稱里正、里吏,後改稱坊正。[74]《魏書》卷六八《甄琛傳》,中華書局,年,頁。[75]張國剛《唐代鄉村基層組織及其演變》,《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册》,—頁。[76]曾我部靜雄《都市里坊制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頁。[77]《令義解》卷二,吉川弘文館,年,91頁。[78]曾我部靜雄《都市里坊制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頁;坂上康俊《論唐代城市鄉里與坊的關係》,—頁。[79]《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二五引,中華書局,年,頁。[80]《通典》卷三《食貨三·鄉黨》,63頁。[81]《舊唐書》卷一五下《憲宗紀》,頁。[82]包偉民《宋代的城市管理制度》,《文史》7年第2輯,氏著《宋代城市研究》,—頁。[83]《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中華書局,年,頁。[84]牛來穎《論唐長安城的營修與城市居民的税賦》,《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9年,91—頁。[85]史念海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唐長安縣、萬年縣鄉里分布圖”,78頁。[86]《通典》卷三《食貨三·鄉黨》,64頁。[87]宫崎市定《中國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國崩壞的一面》,39—40頁。[88]魯西奇《城牆内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的形態與空間結構》第二章《唐宋時期漢水流域州縣城的形態與空間結構》,中華書局,年,—頁。[89]宿白《隋唐城址類型初探》(提綱),北京大學考古系編《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年,—頁。[90]如李孝聰的觀點,參所撰《唐代城市的形態與地域結構——以坊市制的演變爲線索》,《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上海辭書出版社,3年,—頁,又李孝聰《中國城市的歷史空間》,北京大學出版社,年,61—頁。[91]愛宕元《唐代地域社會史研究》一書後附《唐代州縣城郭一覽表》,—頁。[92]詳參魯西奇《“城牆内的城市”?——中國古代治所城市形態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9年第2期,7—16頁;《唐代地方城市里坊制及其形態》,氏著《城牆内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的形態與空間結構》,—頁。[93]魯西奇《城牆内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的形態與空間結構》,—頁。[94]參氏著《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年,—頁。[95]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一閣藏明抄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中華書局,6年,下册頁。[96]參考《天聖令·雜令》唐15條之定義:“州縣録事、市令、倉督、市丞、府、史、佐、計(帳?)史、倉史、里正、市史,折衝府録事、府、史,兩京坊正等,非省補者,總名雜任。”(頁)[97]觀點見渡辺信一郎《北宋天聖令による唐開元二十五年賦役令の復原並びに訳注》(未定稿),《京都府立大学学術報告人文?社會》第57號,5年,83—頁;趙璐璐《唐代“雜任”考——〈天聖令?雜令〉“雜任”條解讀》,《唐研究》第14卷,北京大學出版社,8年,—頁。牛來穎在社科院歷史所《天聖令》讀書班中亦曾發表過類似見解。[98]如武伯綸《唐萬年、長安縣鄉里考》,《考古學報》年第2期,87—99頁。[99]《隋代墓誌銘匯考》,號,—頁。[]辛德勇《隋大興城坊考稿》,《燕京學報》新27期,北京大學出版社,9年,25頁。[]吴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2輯,三秦出版社,年,—頁[]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版),三秦出版社,6年,頁;杜文玉《唐長安縣、萬年縣鄉里補考》,—頁。[]《隋書》卷八《禮儀三》:“在京師葬者,去城七里外。”頁。天聖《喪葬令》唐4條:“諸去京城七里内,不得埋葬。”吴麗娛《唐喪葬令復原研究》,《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頁。[]池田温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年,頁。[]《唐代墓誌彙編》顯慶,頁。[]《唐代墓誌彙編》天授,頁。[]長安、萬年縣下轄鄉里村名的考訂隨長安墓誌不斷出土而持續進行,較新的工作參閲拙文《唐萬年、長安縣鄉里村考訂補》,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21輯,三秦出版社,年,—頁。下文涉及相關鄉、里、村的存在與地理分布皆據此,不再一一注明。[]《唐代墓誌彙編》開元,4頁。[]《唐代墓誌彙編》大和,頁。[]坂上康俊《論唐代城市鄉里與坊的關係》,頁。[]圖版參考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3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年,頁;孫蘭風、胡海帆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北京大學卷》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年,95頁。後者較佳。[]《朝儀郎楊崇夫人甘氏墓誌銘》,藏碑林博物館,李子春《三年來西安市郊出土碑誌有關校補文史之資料》,《文物參考資料》年第9期,54頁。感謝郭桂坤兄提示資料出處。[]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二七,《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0册,頁中。[]《西安歷史地圖集》,78頁。[]《太平廣記》卷三六一(出《記聞》),中華書局,年,頁。[]《長安志》卷一一《萬年縣》,頁。[]坂上康俊《論唐代城市鄉里與坊的關係》,—頁。[]《舊唐書》卷三七,頁。[]《太平廣記》卷一三五《隋文帝》(出《西京記》),頁。[]《歷代名畫記》,秦仲文、黄苗子点校,人民美術出版社,年,62—63頁。[]段成式《寺塔記》卷上,據段成式《酉陽雜俎》,方南生點校,中華書局,年,頁。[]辛德勇《兩京新記輯校·大業雜記輯校》,三秦出版社,6年,頁。[]《隋書》卷四《煬帝紀》,84頁。[]《隋書》卷三七《李敏傳》:“楊玄感反後城大興,敏之策也。”4頁。[]《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73頁。[]西安唐城工作隊在對明德門遺址進行發掘工作時發現,明德門經過二次修建,唐代路面下有早期路面,並有清晰車轍,應爲隋代建成,一直使用至永徽五年後,此後新造路面。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唐長安城明德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年第1期,33—39頁。[]《唐會要》卷八六《城郭》,上海古籍出版社,年,7頁。[]《舊唐書》卷九八《杜暹傳》,頁。[]殘卷藏敦煌市博物館,定名參榮新江《敦煌本〈天寶十道錄〉及其價值》,唐曉峰等主編《九州》第2輯,商務印書館,年,第—頁;録文及解析參考吴震《敦煌石室寫本唐天寶初年〈郡縣公廨本錢簿〉校注並跋》,《文史》第13輯,年,89—頁,京兆府部分見98—頁。[]《長安志》卷一一《萬年縣》記唐四十五鄉,卷一二《長安縣》記唐五十九鄉,、頁。《太平寰宇記》卷二五—卷二七《關西道?雍州》於每畿縣下記舊鄉數與今鄉數,王文楚點校,中華書局,7年,、、、、、—、、、、頁。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ninganzx.com/nasdl/5967.html |
当前位置: 宁安市 >徐暢城郭内外鄉里村坊制在唐長安的實施再探
时间:2021/3/1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元旦3日bull长白山住五星酒店
- 下一篇文章: 青岛宁安路小学学年度第一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