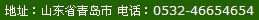|
高铁开通,文化疼痛,奈若何? 文 姚要武 此刻是上午十点,我坐在回老家的火车上——上海到安庆,高铁G,二等座,元。坐在车厢里,翻翻书,喝喝水,看看手机,听身边的人聊天,偶尔听到一口乡音土话,既感到亲切,又忍俊不禁,想学却已开不了口,只好在心里模仿。 安庆高铁站 坐高铁能够直达安庆,要到南京到安庆的城际铁路(宁安高铁)建成通车后。从消息出来到开工,就苦等了很多年;年开建,一再延后,直到年底才正式通车,又是翘首了很多年。差不多有十年,它成了我们心头最大的期盼。 青弋江风貌 望着窗外的风景,沪宁这一段,因为经过得太多,可以熟视无睹了。而一过南京到了安徽境内,就全是新鲜,山山水水,莫不有情有味,尽管两地的城市化水平还不在一个档次上。京福高铁开通时,说它是“中国最美的高铁”,而宁安高铁,沿着皖江(长江安徽段)南岸,经马鞍山、当涂、芜湖、弋江、铜陵、池州,北跨长江抵达安庆。誉之为“最诗意的高铁”,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在我的心灵深处,它有那么多令人痴迷和陶醉的地方。 采石矶 我在马鞍山工作了十年,娶妻生子,无疑是我的第二故乡。它那九山环一湖的园林城市格局,采石矶、朱然墓、雨山湖等风景名胜,无时不让我梦绕魂牵。采石矶,我去过不知多少回,里面的景点、道路乃至竹木,都历历在目——太白楼、燃犀亭、捉月台、三元洞、翠螺峰、李白衣冠冢、林散之艺术馆、常遇春大脚印,还有后来建的望江楼。 太白墓 过了马鞍山就是当涂,过了姑溪河、太白山,就是芜湖、弋江,南边是宣州府、敬亭山。接着是铜陵、池州,南边有九华山、桃花潭,乃至徽州、黄山。这些地名都进入了文化史,八百里皖江,是烟雨的江南,更是诗酒的江南。去年清明期间,我们组队去了一趟宣城,把它兜了个遍,游了广德太极洞,绩溪胡氏宗祠,泾县桃花潭、查济村。青弋江是宣芜地区的母亲河,从黄山流出,出太平湖、桃花潭后,经泾县、南陵,在芜湖注入长江。 没想到,到安庆时,欢迎我的,竟是一场豪雨。下车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出站时,狂风大作,还没走出一百米,大雨倾盆而下,伞都打不住,鞋子也进了水。母亲焦急地给我打电话,叮嘱我不要急着回家,等雨停了再走。其实,我在安庆,她有什么可担心的?我的四年大学,就在安庆上的,高华亭、集贤关、锡麟街、司下坡,哪一条巷陌我不熟悉?沿江寺、振风塔、独秀墓、巨石山,哪一处景点我没去过?巧得很,搭了个家门口的顺风车,四点多就到了家。 桃花潭 享受着便捷和欢乐,可是怎么也忘不了曾经的曲折和困苦。这条高铁开通前,每年回老家,想乘火车,但是很难买到票,全靠妻的一个学生帮忙,她妈妈在火车站工作,把我们带上车,托付给她的同事。晚上上车,我们谦卑地挤在乘务员的工作间里熬一宿。绿皮车又挤又慢,还要绕道。哐当哐当地到了南京,却要从长江大桥过江,向北经滁州到蚌埠,再掉头南下,到合肥后转入合九线,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才到桐城,然后打的回家。 返程时就更麻烦了,再也找不到人帮忙了,全靠弟弟守在电脑前等退票,什么时候等到了就什么时候走,几回都是大年初三。大年初一得到“好”消息,也不过是一张票;初二准备行李,真的连过年的感觉还没找到呢。最为惊险的,是有人扒窗。安庆是劳务输出大市,起点站就上满了人,接下来的桐城、庐江、舒城等站,根本上不了人。火车缓缓进站的时候,就有人跟着它跑。车门一开,就是一场混战。车里的人好奇,推开车窗往外看,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翻进来一个小伙子,吓得我们几个人合力赶紧把窗户关上。 车厢里拥挤不堪,无座的比有座的多得多,他们就席地而坐,瓜子壳花生壳随吃随吐,车厢里弥漫着浓烈的方便面味道。小孩要上厕所,更是苦差中的苦差,必须把他架在脖子上,一步一步地腾挪,一个一个地商量、借步。安徽境内,车子开得很慢,清早就出发,到合肥已是中午,到江苏境内天就黑了,这时才跑得像火车。然而更可恨的事情还在后头,车到上海嘉定安亭后,还要停四十多分钟,让后面的快车先通过。年幼的儿子,此时也学会了不平,称“协和号”为“霸道号”。最惨的一次,加上晚点,到上海时,已错过地铁,打的到莘庄,花了两百元,比一路上车费的总和都多。 高铁1 高铁2 有了高铁后,原来的绿皮车就取消了,离安庆还有五十公里路,又总会带点鸡蛋等土特产,所以我一般选择在镇上坐长途客车,尽管路上费时较多,但天黑之前把我带到上海就行。曾经走过的路线,好像有两条。先都要在桐城上合安高速,朝北往庐江、合肥,在肥东兵分两路,一路往东南经巢湖、含山、马鞍山,走的是合(肥)常(熟)高速;另一路往东,经全椒、浦口,从南京长江三桥过江,走的是沪宁高速。 这一次返程也是如此,直到庐江都没有什么异常。可是一到庐江马堰,突然来了个大转弯,把我搞蒙了,看路标是G3(京台高速)。赶集“搜狗地图”,这是一条全新的线路,我立刻来了精神,就开始记地名,庐江县有沙溪、泥河、店桥,枞阳县有浮山、横埠、周谭、普济圩,最后在老洲过了铜陵长江大桥,再转入G50(沪渝高速),一路东北行,基本与宁安高铁平行。等到在马鞍山转入常合高速,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殊途同归。 庐江、枞阳这两个桐城的邻县,行政隶属关系近年来都发生了改变。年8月,撤销地级巢湖市,所属庐江县划归合肥市;年10月,原本由安庆市管辖的枞阳县划归铜陵市。枞阳的改宗,在朋友圈内产生了极大的争议。 枞阳县 “搜狗百科”查“桐城”和“枞阳”的“历史沿革”,二者都有一个关键年份和相同表述:“至德二年(公元年),改同安县为桐城县。”接下来从五代一直到民国,枞阳都“为桐城属地”,直至年2月18日。 小时候,就听老年人讲,枞阳原来属桐城,但并不放在心上,因为这不干我的事。上高中后,高一时地理老师带我们去枞阳浮山进行地理考察,高二时换了个语文老师,五十多岁了,自我介绍时说是枞阳浮山人,听口音就和我们不同。通过他,我才知道了桐城五大姓、桐城派三祖、六尺巷、三里街、龙眠山,才知道教学楼前那棵几人合抱的银杏树,原是姚鼐故居“惜抱轩”前旧物……高三时某一天人头攒动,说是知名校友、外交家黄镇回到母校了,后来他又去浮山中学了,那里也是他的母校。 安徽省桐城中学 上大学后,辅导员是枞阳人,从他嘴里第一次听到“枞阳出人,桐城出名”一说。晚上卧谈,两地同学就此话题展开论战,我才稍稍明白一点其中的是非曲直。你尽管有不平,但古代文学课上的“桐城派”怎不能改成“枞阳派”吧;可是在现代文学课上,我们就被戴上了“桐城谬种”的帽子。算是打了个平手。 参加工作后,特别是来上海后,老乡的外延随时发生变化,除了三个安庆人在一起,桐城人和枞阳人不算老乡,否则都算。可惜这种甜蜜,在年10月戛然而止。犹记当时一位兄台问我对此事有何看法,我的心态一下子就失了衡,认为他有挑衅的味道,于是出言十分不逊。从此,酒桌上,只要有这两地人同席,总有人以此话题打趣我们,我们会一下子酒兴全无,满嘴苦涩。从此,和枞阳的朋友在一起,我们似乎都会刻意回避这个话题,所以也就生分了许多。 安徽省桐城中学校园内一角 桐城和枞阳一千两百年来本为一地,即使解放后分立,但毕竟还在安庆这个母体之内,同学之间偶有纷争,不过是兄弟阋于墙。可是如今将枞阳划给铜陵,触及了我们的心理底线,制造出一种撕裂的疼痛。就在昨天,校友群里还有人在发《“枞阳出人,桐城出名”一说不能成立》的帖子,尽管它的论证并不精审,但我能理解他的感情——三年了,伤痛还在。可是我已经比他通脱,这样回复他:“历史地看待‘桐城’这个概念,就没啥问题。” 仔细想来,这种文化的撕裂,的确是由行政隶属的改变造成的,但这种改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发展经济是主因,宁安高铁也是源动力之一。安徽要发展皖江,所以要有这条高铁;有了这条高铁,沿江各市的发展空间就需要拓展,跨江发展就成了模式。巢湖市被撤销,合肥、芜湖、马鞍山各分得一杯羹,铜陵呢?把对江的枞阳划过来,似乎顺理成章。在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性”时代,谁还会顾及文化或者“桐城派”? 原来,乘高铁的获得感和文化撕裂的疼痛感之间,竟然存在着隐秘的关联,就像硬币的两面,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正如歌中所唱的:“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 ▼ ?????? 约稿启事地名古今”以强调原创为主。内容板块和栏目大致如下,文章字数以两三千字以内为宜。突出个人化,文字尽量讲究而有韵味。 1、我说地名|以个人视角讲述熟悉的地名历史变迁和故事,避免面面俱到,避免罗列概念。突出个人对地名的理解和历史变迁的解读。 2、倾听讲述|每个村庄、每个街巷,都有说不完的人与地名故事,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倾听讲述,以细节勾勒岁月流逝中的、难以重现的故事。 3、我的漂泊|许多人的人生旅程,会在迁徙、漂泊中走过。用印象最深的几个地名,穿插个人的成长史、生活史,本身就是地名古今不可缺少的内容。 4、故居寻访|千百年来,每个地方都有影响历史、文化的名人,故居寻访,在寻访中解读名人,使之古今融合。同样避免面面俱到,写最能触动自己的地方即可。 5、行走天下|旅行已成为当今时尚所在。如何行走,如何把旅行化为自己生活、精神的一部分,把旅行与异地观感融为一体,既是游记,也有颇为充实、敏锐的诗意表达,这是最值得期待的行走天下。 6、回家的路|远离故乡的人,心中永远牵挂故乡。每次踏上归家之路,会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儿时的星星点点的记忆,家庭几代人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一棵树,一口井,一家人,左邻右舍,都是故乡难忘的记忆。 “地名古今”的作品,将根据相应版块予以结集出版。欢迎各位新老作者赐稿,图文分别打包发送,请发:lihui vip.sina.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ninganzx.com/nasdl/9614.html |
当前位置: 宁安市 >姚要武倾听讲述高铁开通,文化疼痛,奈
时间:2022/4/2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招聘通知中宁县年秋季ldquo
- 下一篇文章: 最全年衡水市区小学初中片区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