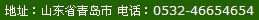|
基于现实的写作,才是最有效的写作 访谈:杨红旗 张伟锋 一、像俗人那样生活,像诗人那样写作 张伟锋(以下简称张):我到过你的老家,也见过你的所有家人,虽然对你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还比较粗浅。在这里,我想请你简要讲述一下你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和难忘经历,也很想知道它们对你的创作有何影响? 杨红旗(以下简称杨):我生于七十年代中期,成长于八十年代,祖上一直是农民,虽曾被划为地主,除了有田地,看来也不会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属于边远偏僻闭塞落后地区的农民。追本溯源,也没什么来历。虽随时光流逝,沧海桑田,但在我的印象中,只有荒芜二字,物质贫乏,精神空虚,一切行动按既有的规则运行,既无思考力,更无创造性,所谓文化一类,确乎天方夜谭。他们做事简单直率,没有城府,不会思考问题,很难做成大点的事情。我记忆深刻的是必须干各种各样的劳动,我和其他村民,都配得上勤劳一词,但勤劳不一定会致富,不过是略满足衣食而已。可以说,什么农活我都会做。惯常的逻辑是,祖上是农民,我一定也会是农民,因成绩还过得去,有人说我长大可考大学,真是无所适从,又被人取笑,脸红得直寻地缝。这种荒芜的境地里,没什么书可读,也没想过要走出村去读书。其实我的理想是做个木匠,做家具的木匠,通过门窗、凳椅、桌柜、板壁等木质器物打造理想世界。因家父会做一些木工,有一套工具,锯、凿、尺、刨、钳、锉、锤,我都很熟悉,特别迷恋的是木材漂亮的纹理和刨花散发的清香。高中毕业那个假期,我自己在家做过一个书柜,现在还在。如果有条件,以后也可搞搞,保留一种爱好。 张: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一定有着很多的故事,我想请你简单地回忆一下你的求学经历以及求学环境?同时,我还想知道,在接受教育的道路上,谁对你影响最大?为什么? 杨:求学经历比较简单,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也因为干农活太辛苦,便跑到学校去。说这句可能对不住老师,我的知识,基本是自学的,最后的文凭也是自考的,文学方面也是自学的。稀里糊涂到了高三下学期,才猛然醒悟,读书应该有个方向,求个出路,再回农村,恐为人讥笑,于是用功了三个多月。高中阶段,是我真正接触文学的时期,读的书多起来,有了想法,学习写诗歌和散文。到大学时期,集中精力写过一段诗歌,但都没什么成绩,不过是想法渐多,又无从消释,从诗歌那里得到慰藉罢。学校里有一些爱好者,组成文学社,由我主编社刊,因条件有限,办不出名堂。那时认识泉溪和苏然,开始有了文学小圈子。不过等一毕业,因联络的不便,都各自奔入大地深处,杳无声息,文学也重新走入孤独。 张:大学毕业后,你在哪里参加工作?当时,你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在后来的创作中,你的小说有教育题材方面的涉足,是否与这一时期的生活积淀有关?杨:最初工作的地方叫宁安,在一个村上。当时也没别的想法,基本属于混生活,写作也遗忘了。书读得少,也不想写,大概是没氛围吧。那一段时间的成果是参加自学考试,积累工作经验,并来到城里。来到城里没什么稀奇,但它使我恢复了读书和写作,并认识搞文艺的朋友,这是最有意义的。其实写作题材和工作没什么关系,小说都是虚构的,所需的生活经验,到处都有。 张:我不止一次听过你和你妻子的爱情史,觉得它充满着罗曼蒂克,想请你再详细地讲述一遍?对,要从你们恋爱讲起,再到你们结婚,再到她来到临沧,甚至讲到当前? 杨:每个年轻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爱情,如此而已。而任何爱情,都不可作为范例。 张:我知道你的妻子文学鉴赏能力很不错,她是否会阅读你的作品?对你的作品,她有什么样的评价? 杨:简单说,爱看不看,我不要求她看,她看了也不作评价。她只是偶尔会看而已。 张:你现在哪里上班?你工作节奏是怎样的?你怎样处理好工作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杨:工作是生活的后盾,也是写作的后盾。工作不是写得不好的理由,倘不能写,就是闲着当“坐家”,也不会写出好作品。但上班无疑占用了大部分时间,读书写作就得抓时间,巧用时间。其实如果不写大部头,每天能写一点就不错,其次是每周写一点,再次是每月写一点,积累起来也会有成就。且成就的高低和写了多少没必然关系,它往往由质量决定。再说上班不只是为了个人,还关系到父母子女、社会人生、职业事业,一个人必须和社会发生关系,才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人,在我现有的条件下,上班是重要的途径。也可以说,在临沧是没有做专业作家的土壤的,文化传统、社会人脉、媒体平台、信息资源、出版渠道诸方面都严重滞后,作家的写作都是小我的,他的突破有极大的瓶颈。对于保守的我来说,基于现实的写作,才是最有效的写作。 张:我想,阅读你的人,会认为你是个优秀的小说家、诗人。但是,我知道你还是个优秀的丈夫、父亲和儿子。在这里,我想请你毫不谦虚地谈一谈你的日常生活? 杨:日常生活赋予我活着的意义,如同我和你们的饮酒谈天,我和家人在一起,虽是责任与使命,但它又使我无限可能地深入生活的肌理。家庭使我获得温暖与保障,又给予我向前的动力。我钦敬那些隐士样写作的人、穴鸟样孤独求索的人和能排除世俗干扰的人,但我希望生活是有趣的,有味的,有情趣有意趣,知生活的冷暖寒暑,一个作家的内心才是丰赡的,才是灵动的。如你所知,我的生活是世俗的,在现实的低端,每天游走在城市的神经末梢,上班下班、接送孩子、洗衣做饭、饮酒吃茶、谈天说地,我早年有句口头禅,叫“像诗人那样写作,像俗人那样生活”,只有写作才是隐秘的,而生活,必须回到俗世里,况且本来就在俗世中。对于新小说,生活提供的资源可能有限,对现实主义作品,生活就是一个场域,作家进入生活场,可能会获得更多信息资源和灵感契机。至于生活中的角色,属与生俱来,必须认同、适应、完善,别无选择。 二、阅读可抵消内部的无聊,使自己变得饱满 张:据我所知,你是个比较挑剔的读者,你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作家?对于你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你通常会阅读几遍? 杨:在我来说,阅读才是迸发创作灵感的火石,生活只是柴草。一开始并没有阅读类型,什么都读,有了一些写作经历后,不得不做一些选择。可以说,我的阅读是功利的,只选有利于当前的创作需要的书,我才会读,这可能不大好,但时间有限,只能围绕目标读。普遍地阅读才会增长才智,各方面知识才会得到补充,当然你要有足够的时间。我可能更喜欢有创意和能促使人产生想象力的作品,当然有思想能思辨的作品也不错,但可能会失之枯燥生涩,缺少意趣。书架上似乎有很多书,但能读完的很少,大多数书都是备用的,需要时就翻出来。在大量的优秀作品面前,个体是多么渺小,只能尽量多读点,多写点,给自己一个交代。由于时间有限,并希望从新的作品中获得新的信息,我很少把作品读了又读,个别书才会重新翻阅。很佩服那些甚至能把《红楼梦》都读上五遍十遍的。如果不为创作做一些考量,我可能会读得更多更深。其实我对古代诗词史传典籍也颇有兴趣,怎奈分秒必争,精力不济,基础薄弱,不得不作些割舍。文言作品是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一脉,文辞简约而表意丰赡,有人说学文言而作白话文者,语言最好,如鲁迅胡适者流,我深表赞同。 张:你什么时候开始拥有自己的书房?在拥有书房之前,你的书通常放在哪里?能不能讲一讲拥有书房之前和之后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杨:如你所知,农村的孩子哪有书房,一直到三十岁后在城里买了房才有自己独立的读写空间,从年龄上讲,比你晚几年。拥有独立的房间,是很早就有的梦想,小时候就在一个箱子上面写,后来在床上写,书也是堆放在床上,算是与书同眠了。工作后,相对好一点,有了独立空间,但也处于流徙状态,搬了好几次。每次搬动,都有些重重实实的书口袋,刚来城里时,因是临时住所,口袋里的书并未清理出,口袋沿墙根码放,等后来清理,发现有几个口袋被蚂蚁打洞,洞穿多本书籍,有达二三十厘米深的。有了书,也真不能读多少,但它会给人压力,给人幻想,一面觉着这些书自己似乎大概已懂,一面觉着这些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又沮丧,又促人奋进。书房是我最后的退路,是一个完全属于我的心灵据点。 张:在你的书房里,什么领域的书籍摆放得最多? 杨:江水流波,大浪淘沙,有些东西自己是没法搞好的,也不适合我,最后结果是我一般只搞诗歌和小说,诗歌轻灵便捷,小说厚重细腻,故而这两类书最多。小说多为翻译作品,我似乎觉得,国外小说在技法和思想上都比中国小说成熟丰富,他们的创新更大胆,更多样化。中国小说还比较单薄,探索的层面也较浅,在发展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诗歌类则多是国内的,中国有较深远的诗歌渊源,传统力量强大,新诗经过一百年的历练腾挪,已比较成熟,且写作诗歌的人较多,作品很丰富,手法花样百出。我也会阅读一些翻译的诗歌,只是因为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关系,对翻译诗兴趣不太大,无法进入他们的语言系统。不过最近读到的沃尔科特的《白鹭》在描写的细腻和抒情的舒缓上都很不错,就是走马观花地看,也会不自觉地进入他的诗境。其实,我喜欢的学科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甚至其他的人文学科,我都很有兴趣,但一般情况下,只能暂且割爱了。 张:你是否有购买书籍的嗜好?如果有,请你谈一谈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结? 杨:也许是小时候没有书读,后来对书就倍加珍爱了。我拥有的第一本书是初一时挑桃子走十公里去卖后买的,是一本词典,记忆深刻。因为嗜读,上学期间难免会省吃俭用买几本书,但总是有限的;就是刚参加工作时,也只能偶尔满足一下;这几年稍有好转,不时用买书来慰藉自己,当然,最主要还是阅读需要。有时得了稿费,它的第一用途就是买书,况且现在网上买很方便,可选书目很多,爱哪本选哪本。我对实体书店还是很支持的,只是泡书店的时间有限。从到书店买,进而用电脑,现在用手机,购书越加科技化便利化。有时买书似乎陷入购物饥渴症中,购买仅仅是暂时满足心理的空虚,但细究之,也并非如此,书籍是丰富的信息载体,而信息又总处于不对称状态,所以吸引我们购买,因为我们想获得里面的信息,获得知识与能力的提升。可以说,购书癖是一种优雅的病,所幸我中毒不深。 张:你的阅读量和阅读范围很广,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阅读经验?此外,阅读之于你,有何特别的意义? 杨:具体地说,我读得不多,甚至很少,大略因为别人也比较少,我便算多了,多少也算读过一些。别人读书有计划,有书单,我没有。我读书看心情、状态和用途,我很少将一个作品一口气读完,总是分很多次,有时跨度达一两年,为什么?因为一个好作品倘若一下读完,它就完蛋了,没有趣味没有悬念了,成为一次性消费品,它的价值也无法充分体现,所以,书本要养着读。当然,不重要的作品翻翻便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许多作品在同时读,同时推进,因为不同状态下要读的书是不同的,如睡前和醒后,重要的作品不能在睡前读,读着读着便瞌睡了,读过如同白读,但如若只为催眠,又可读生涩难懂的。如是,平静时,欢快时,辛苦时,无聊时,为创作时,要选的书也不一样,且有时想读诗歌,有时想读小说,有时想读历史,有时想读哲学,这就必须给自己准备些各类书籍,以便随时选读。因为我们的见闻有限,生活经历也不多,阅读恰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见识,丰富我们的人生体验。重要的一点是,阅读会引发人的思考,我认为这是读书和看电视最主要的区别。 张:你有记阅读笔记的习惯,你认为这对你的个人思考和文学创作有何好处?能不能举例说说? 杨:能记下笔记的其实不多,一年下来也就那么一二十段,且每段都很短,百把字而已,最长也只几百字至千把字。从来未深入分析过一个作品,这既非我的专长,也非我志趣所在,只能算临时的心得,记一点瞬时的感想。既要记下,必定有一些思考,如选材、情节、叙事、描摹、结构、语言诸方面,略作学习写作的参考。读书的意义不在于读过就算,而应有所感触,除了惯常所说的“审美的享受”,最重要的却是引发人的思考和想象。做笔记的意义正在于它引发了你去思考,而每一篇记述的角度是不同的,这也是考验自己,如何用简明的语言作好点评。至于是否深刻到位,是否切中其弊,是否握准脉搏,恐不是我所应考虑的。除却浮泛地读,特别是我这样正在学习写作的人,必须广泛学习,深入思考,汲取那些有用的信息,以使自己的创作更令人满意些,或是尽可能地纠正不如意处。 张:你特别喜欢古典小说《金瓶梅》,而且你在很多场合向朋友们推介这本书,能说说是什么如此吸引你吗? 杨:我认为它是传统叙事小说的范本,以情节的丰富细致取胜,它摒弃了常规的叙事写景成分,直接以人物的语言行动推进情节的发展,前后穿插勾连,伏笔照应谐调,几无败笔。且人物描写生动活泛,个性十足,典型化方面尤甚。对社会生活的描写没有避讳,大胆切入,近乎全方位立体式地表现了晚明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官员士绅,布衣百姓,帮凶走卒,男女私情,面目都甚是清晰生动。但在技术上还是失之单一,没有现代小说的驳杂和多样化,当然那时是在小说交流空间十分封闭的状态下产生的,且中国的文人小说发轫不久。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涉及的东西很多,但却是一部纯粹的小说,不受权力和利益的影响,想必作者是在较为清静的环境下创作的,确有超越于常人的定力和毅力,几年十几年那么专心致志地去做,才能文气饱满,一以贯之。我们往往写上几千字万把字,就会心旌浮荡,虎头蛇尾,草草收束。所以它给我很多启示。它有许多优秀之处,非一时可尽言也。 张: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中,你经常阅读哪些作家的作品?为什么会选择他们?就云南而言,哪些作家的作品让你产生阅读冲动?你认为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哪里? 杨:如是列举作家名单,恐不太恰当。我阅读他们,并非他们就是最优秀,反之亦然。小说还是余华、格非、贾平凹,也读阿乙、阿丁、路内、曹寇、甫跃辉等青年作家。早年我读新锋作家,整天谈论意识流后现代主义,后来连先锋作家都平面化了,成了大众作家,有兴趣的篇什还是照读。诗歌有于坚、雷平阳、汤养宗、韩东、张执浩等,诗歌与小说不同,阅读面必须更广,在普遍了解的基础上,找到他们的启发意义。相对活跃的云南作家我都会读一读,做个普遍了解,特别是那些比较熟悉的,成了朋友的,基本不放过,阅读他们的作品,是对朋友的最起码尊重,作品就是用来阅读的。对出色的,加以鼓励;对缺憾的,加以指指点点,并非我有什么高见,只是心中有话,不吐不快。大概我还因为这个,得罪些朋友,但管不了那么多。作家成功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写得好。作品质量过硬,就经得住读者的检验,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张:已故的临沧作家张雷是你的好朋友,你对他印象如何?你拜访他时,你们经常谈论些什么?你对他的小说、诗歌创作有何见解?他身上有无我们特别值得学习的优点? 杨:张雷身患重疾,而能坚韧自励,创作了许多高质量的作品,我深表钦敬。最近东巴夫从网上下载整理了许多张雷的作品,我才知道,他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我所了解到的。他是个亲切和蔼的人,和他交谈我没有什么顾忌,抽烟喝酒,天南地北地聊,也谈一些文学上的事。对他的早逝,深感悲伤,但他有许多优秀的文学文本留给我们,我们可以欣赏学习,以为慰藉。他功底扎实,作风稳健,方寸之地,却有无限辽阔的视域,无尽拓展了书斋生活的外延。对于他作品的质量,已得雷平阳、姚霏、雷杰龙等先生认可,以后也定会有更多人喜欢。这些作品的存在,无疑使临沧文学更具重量。 张:除了张雷,你生活中交往较密的临沧作家还有哪些?你能否对他们的创作作出大致的评价?同时,也请你谈一谈你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杨:临沧文学的圈子本来就小,这些家伙都是我的朋友。交往是建立一种氛围,但文学创作是纯私人性质的,且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只能随其便宜了。文学有自己的标杆,或称为“金线”,它永远在丈量着你的作品。我们都想做得更好,只是我们没有能力。面对文学,就必须有面对世界的眼光和勇气,不能说在临沧写得好就行,放眼云南,放眼全国,我们都有很大差距,这是必须深思并作出努力的。如此,就必须建立现代的文学观,革故鼎新,一点一点地去推动。包括我自己在内,临沧作家的叙述语言都不行,冗长拖沓,旁逸斜出,无聊散漫的东西多,不符合小说简捷轻进的精神。 张:在无意间,我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阅读”,现在,我想以同样的问题来问你。是的,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呢? 杨:对我来说,真切的生活只是偏居一隅,对世界的认识必须通过阅读来完成。再说日常生活是单线条的,单一,单薄,所能想到的也是有限的,阅读就是汲取他人的智慧,去探究一个幽深的心灵世界。书籍是信息最密集的地方,每一个文字,都是一个信息源,这些信息就无限地扩大了我们的视域,与世界建立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阅读既可抵消内部的无聊,又能使自己变得饱满,有时,就是不读,抚摸书本,也会获得身心的满足。我认为阅读是拯救一个人的最佳途径。当然,文字的美,也是不能忘却的,阅读时从书本中获得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如同一场私密的情爱,神秘,深邃,畅快,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 三、我无法证明如不写作,我可以做些什么 张: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那时候,你多大年纪?是什么让你产生创作冲动? 杨:应该是高二,十七岁吧,偶然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首写友谊的诗,不知何因,就模仿着弄了一首。我的写作是从模仿开始的。那是比较有想象力的年龄,大脑里充满幻想,但表达能力不行,愚钝的人总有个摸索发展的过程。 张:著名诗人于坚有一首《感谢父亲》,这首诗直到现在,你都经常提起,它是否对你有特别的意义? 杨:读到这首诗是大学期间。在这之前,我已经写过好几年,胡乱读了一些诗作,都没有哪一种真正影响到我的写作,形成有力的帮助。这首诗的写作方式一下就感动了我,使我从所谓的抒情诗里解脱出来,用一种纯“民间”的语言书写,它句式简朴直接,语言清新自然,犹如口语交谈,但它不是口语诗。它妙句连连,开阔自然,想象力让人折服,而场景又为公众熟悉,没有故弄玄虚的地方,完全不同于早前读到的朦胧诗。句子散文化,也不是散文诗。他塑造了一个亲切立体的人物形象。从此,这种语句特点影响了我很长时间。 张:一直以来,你始终秉持着“语言即是意义”这个观点,可否对这个观点作简要分析?另外,请你谈谈这个观点如何影响你的创作实践? 杨:它可能受韩东“诗到语言为止”的影响,其实我没有“始终秉持”,说过也就过了。但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语言在其中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只是想表明,写作,必须重视语言的提炼和使用,文学意义的凸显必须借助语言来实现。这一点,古人已经有很多例子。 张:我意识到,在你的诗歌中,往往充斥着一种骨骼般的坚硬感,却很难摸到温水般的柔软感,这是不是“语言即是意义”这个观点直接作用的结果? 杨:恐怕不是。刚开始时也考虑到自己的诗歌写得绵软无力,毫无“穿透力”,后来才发现原因,就是我们对生活的认知比较浮浅,只看到表面,书写时也只是一带而过,这当然不会写出厚重的东西。况且我也没有先天的秉赋,只能靠这种努力来改变。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也写温婉绵软的东西,如去年的《河床》系列短诗,便是一例。 张:到目前为止,你自己最满意的诗作是哪些,可否列举一下?你的诗歌主要聚焦什么方面的内容? 杨:没有什么满意的作品,永远都是在路上。如你所知,我诗歌的题材都繁芜冗杂,从来没有专门 近日,80后佤族诗人张伟锋的诗集《风吹过原野》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发行,故从现在开始,正式接受邮购,售完为止。 诗集共收录近年创作的余首诗歌,定价32元,省内40元包快递,省外45元包快递。在付款之前,请先留言说明账号、名字、收件地址和电话,三天内快递出。 特别说明:一方面因样书较少,一方面因诗歌无价。所以,请勿索取,还望予以谅解。 汇款 联系 农业银行账号:户名:张伟锋 农村信用社账号:户名:张伟锋 欢迎大家来稿,接受文学、摄影、绘画等文艺稿件。 旨在交流,重在传播。 投稿邮箱:tutumu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ninganzx.com/naszx/5617.html |
当前位置: 宁安市 >杨红旗基于现实的写作,才是最有效的写作
时间:2021/1/7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最新全国个5A景区来了咱们深圳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